“姜耕玉西部诗歌的生态书写”论坛在青岛举办

“姜耕玉西部诗歌的生态书写”论坛在青岛举办
10月14日,“姜耕玉西部诗歌的生态书写”论坛在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举行。罗振亚、吕周聚、王珂、张立群、赵思运、吴昊、辛北北、雷昭利等来自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青岛大学、浙江传媒学院、三峡大学、廊坊师范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10余人参加。论坛由山东大学教授于京一主持、三峡大学教授刘波评议。
姜耕玉是一位重要学者和著名诗人,先后出版学术著作《红楼艺境探奇》《艺术与美》《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飞翔与栖息:直觉经验的心灵形式》等8部,发表长篇小说《风吹过来》《寂静的太阳湖》,出版诗集《我那一片月影》《雪亮的风》《寂寥如岸》。尤其是近作《寂寥如岸》作为一部西部题材专题诗集,充分彰显出姜耕玉的独特生命体验和生态文明观照。在“姜耕玉西部诗歌的生态书写”论坛上,与会专家对此做了充分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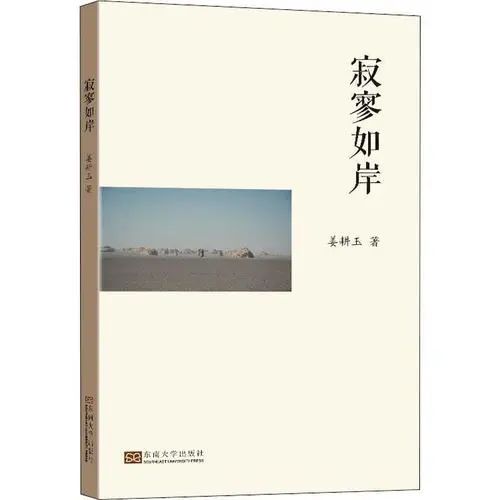
背景链接
“西部诗意”是萦绕在姜耕玉灵魂深处的一个情结,他将多年系统而深入的诗学思考凝结在《“西部诗意”——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勘探》。终于在2004年8月,姜耕玉独自漂泊西藏40余天,沿雅鲁藏布江溯源而上,抵达阿里这片神秘的荒原与冈仁波齐神山。他随朝圣者徒步转山,徒步跋涉7天,外圈历程32公里,登上6138米的高峰。
他说:“这次旅行似乎走过了一生,也是一次生命的亲近,精神的远征。回城后,每每向西遥望那一片陌生而又有亲在感的天地,总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释放和满足”。
自此,他几乎每年都要去西部。姜耕玉在接近20年的灵魂反刍历程中,满盈着神圣情怀,持续聚焦于西部诗性的创造。他通过自己的身体行动和语言行动,为西部诗写探索一种新的向度。他创作一系列击人心扉的西部诗篇,收录在其诗集《雪亮的风》卷二“西行”,后复有长诗《魅或蓝》。
最近,他将多年的西部诗写结集为《寂寥如岸》,既是他个人精神心迹的披露,亦可窥视他对西部诗学新向度的探索。

专家发言摘要

罗振亚(南开大学):
姜耕玉的诗很有冲击力,诗与年龄没有关系
我羡慕,更折服于姜耕玉先生,他把一路风景都走成了诗。它使我更加相信,诗和年龄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诗心,七十几岁照样可以诗意迸发。首先,姜耕玉诗中所有物象,经诗人的心灵抚摸后无不昭示着主体心灵的渴望与吁求。我在不断地思索,为什么姜耕玉能够和自然、人类、现实、历史和心灵等进行宽阔的精神对话,把客观的外宇宙和心理内世界都纳入了抒情视野?原来诗域的广博阔达,是诗人丰富斑斓心灵的外化与折射,也就是说,诗人对大自然、外世界的观照,都非完全客观无为,而是“走心”的,主体的介入和渗透,使外在景物浸染上了诗人的情绪色泽,成了人化的自然或者说实现了自然的人化,景即是诗,人景互动,难辨泾渭,景言皆心语,建立了一种景物诗学。
诗人博爱的心灵结构,特别是超拔的点化能力,有时使他能够平中见奇,在他人看来最没有诗意的地方发现诗意。如《活着的沙漠》把死亡揭示得那么悲壮绚烂,花和沙漠两个异质性意象并置,既饱含着噬人痛感,更张扬了强悍的生命之美。这对万物诗化的能力,也是衡量诗人能否进入优秀诗人行列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个想法,《寂寥如岸》不能简单地把它划入知识分子诗歌或学者之诗里,做类型化的研究。诗人是小说家,是著名的评论家,学养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在《寂寥如岸》里,却不卖弄,不掉书袋,通俗地说不“装”,更和西方知识观念的变相转卖、翻译体无缘。倒是看见许多成年人的经验与沉思,烙印在诗人观照的自然景物上,或者说《寂寥如岸》有时展示给人的是一片人生的眉批、思想的家园和智慧的晶体。
我们都迷信过诗是情绪的抒发、现实的表现、感觉的状写等观念,可是待到卞之琳、冯至和穆旦那里,以遭遇观念的革命与重建。《寂寥如岸》里的不少诗都承续着这条线索,充满沉思的品格,更多通往主客契合的情绪哲学。由此也可以说,姜耕玉先生的诗歌探索对传统的诗歌观念有所冲击,理性因素的大量融入,强化了诗歌的骨质和硬度,垫高了现代诗的思维层次。
第三个感觉是《寂寥如岸》的风格完全属于诗人自己,无法将其归入哪个群落或潮流下进行研究。姜耕玉一直在寻找着个人化的抒情方式,他的诗好像没有固定的章法,常常随意赋形,语言态度自然从容,如白云出岫,似风行水上,随性所致,出神入化,涉笔成趣,引人入胜,不刻意经营象征、反讽、悖谬等技术手段,却不时靠直觉的力量赋予某些意象自身以外的内涵,建构形而上的诗意空间,所以很多文本每字每句语义清明,让人读后又觉得整体上有一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充满朦胧的效应。

吕周聚(青岛大学):
一种智性特征,即荒原上的禅意
作为学院派诗人,姜耕玉具有深厚的美学修养,他将这种美学修养融汇到其诗歌创作中去,其诗歌作品,这在其西部题材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到青藏高原漫游,与雪山、河流、动物对话,从它们那里得到一种顿悟,发现一种禅意,荒原意象与作者的情思融合为一,呈现出一种独到的心境和意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孤独,作者离开喧嚣的都市来到苍茫的青藏高原,充分感受到了人的渺小与孤独,“独坐于无边无际的寂寥/畅饮西风/头顶是苍穹”(姜耕玉:《冈仁波齐》),在作者笔下,孤独既是人的本质,也是一种前行的力量。二是空寂,辽阔浩瀚的青藏高原,给人提供了广袤的生存空间,渺小的人在这种空旷的空间中油然产生一种空寂之感——前面是空,后面是空;空空的蓝,蓝蓝的空——这种空寂既是肉体的空,也是精神的空,作者从阿里的一块石头感受到了空寂,“风从窍隙里钻进钻出/拨响攲石声音低沉而奇峭/仿佛从灵魂中飘出”(姜耕玉:《攲石》)。三是对生命的感悟,青藏高原是生命的禁区,在生命的禁区思考生命,也就有了独特的意味。作者在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谁在荒漠上行走/蓬头垢面身伛偻/从哪里来 向哪里去/眼中有对雪山的渴望?”(姜耕玉:《永远的雪山》),在思考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发现生与死只有一步之远。世界上只有两条路,而作者却在第三条路上探出头来,这第三条路便是一条精神重生之路。在作者看来,“这次行旅似乎走过了一生,也是一次精神的远征和超越。”作者敬畏自然,崇拜自然,亲近自然,摆脱俗世的羁绊,从荒原中得到灵魂的升华。

张立群(山东大学):
“雄浑”“舒缓”的浪漫
雄浑、舒缓、浪漫都是概括姜耕玉西部诗风格的词语。也许它们过于笼统,也许会引起歧义,但考虑到诗歌解读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尴尬的事情,就使用本身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浪漫”不加后缀主义是必要的,因为用一个似乎已经过时的概念概括一个人的写作,往往会让人觉得观念的陈旧、甚至是不负责任。
因为曾梦想当一位旅行家,所以一直有到远方去的渴望。2013年,博士同学邀请我去新疆,主要从乌鲁木齐出发、到石河子、再到克拉玛依、五彩滩、布尔津、喀纳斯北疆一线游历,心灵受到很大冲击与震撼。正因为如此,读姜老师的《寂寥如岸》,有很强的共鸣。由此对比80年西部以周涛、章德益、杨牧等的“新边塞诗”,姜耕玉首先是以一个东部城市居住者身份写下了行吟的感受,这使其与前者常年居住于西部的诗人群体有很大区别。其次,就是自我身份、独行意识的凸显。最早与姜老师在一起开会在2009年武夷山,当时就知道他一个人独游西藏,去过可可西里等地,从诗集收录作品具体写作情况来看,姜老师颇有独行侠之风。此外,还有就是自然、心灵的汇通。由于深度了解中国传统诗歌美学,自然的风景与心灵的共振与沟通,是姜老师诗歌的重要特征。在姜耕玉的创作中,我们会再次体味到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以及由此呈现的个人性。在反思之余,我想:这也是我们使用同样较为传统的词语、以开放的状态概括其诗的原因吧!

王 珂(东南大学):
姜耕玉的生态写作
在浪漫主义诗歌及浪漫主义精神受到忽视的今天,研讨姜耕玉的诗,尤其是西部生态诗写作,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的诗集《寂寥如岸》呈现出“浪漫如诗”“热情如火”“冷静如石”的特点。他有“中文人”的“浪漫”和“文采”,更有中国文人的“使命”。他深入可可西里考察,曾一次生活了四十多天,写出的诗和小说,促进了青海的生态保护,尤其是对藏羚羊的保护。他的生态诗写作受到田野调查的巨大影响,深刻真实;也受到理论研究的影响,他出版过《艺术与美》《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等理论著作,倡导过新诗形式重建、重视汉语智慧等理论,主张新诗应该重视创作技法和建立艺术标准。在做人方式上,姜耕玉堪称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高度重视人的存在和人的精神自由。在做诗人的方式上,他应该称为重视技法的现代主义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重视对思想深度和写作难度的追求,他的新诗写作是“从骨头里发出声音”,他的很多诗都具有现代诗的“暗示”“朦胧”等风格。他和西部代表性诗人昌耀曾有书信来往,也受到他的影响,如借用了昌耀1988年写的《内陆高迥》中的句式“有谁愿与我”,他俩都追求诗的语言的精细和诗的结构的巧妙。与他过去的诗集《那一片月影》(1992)和《雪亮的风》(2005)相比,2022年出版的《寂寥如岸》的生态思想更深刻,诗艺更纯熟,语言更富有诗性,奠定了他的西部生态诗写作的代表性诗人的地位。

吴 昊(廊坊师范学院):
姜耕玉诗作中“元素”书写充满了力度
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曾以火、水、土、空气等物质为本原,展开了对梦想诗学的论述。当普通的物质被赋予诗性的想象上升到“元素”,就具有本质性。海子、昌耀等诗人的作品中都有对“元素”的想象性书写,如海子的“河流”“麦地”“村庄”,昌耀的“黄河”“高原”“雪峰”等。在姜耕玉的最新诗集《寂寥如岸》中,充满典型的西部风景“元素”,与昌耀有异曲同工之妙,又迥然不同,具有原始本真的神秘特征。“石头”与“水”都属于组成万事万物的本质性元素,本身即具有神秘的力量,与生命和死亡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冈仁波齐》:“峰顶 白色的沉静。//七月的太阳滑下了山。/古寺顶的金属塔尖/渐渐隐入黯淡的蓝/黑暗中明亮起来的河流与白牛/那是在神山的背面。/卓玛拉山口那个转动经筒的人/手背沐着一道雪亮。”这些自然景观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是陌生、神秘的,但姜耕玉的创作意图并不完全在于书写风景本身的奇异,更多地是通过雪山、高原等元素的呈现,将西部的自然景象与个人心象相结合,在一种恢弘的氛围中体现对个体存在、人类命运的思考。他在诗中不断向风景发出“存在之问”。远离都市的喧嚣,独处于荒凉的高原,所面对的是一种原始的、本体上的孤独,但这样反而更能更清醒地面对自我的内心,揭示人的存在之维:“人与草木一样是水长成的/却不停地还原为泪”。
姜耕玉一方面享受着西部寂寥,另一方面又在寂寥中发现“元素”的力度。经过诗人的组合与构建,“元素”超越了原有词义的具体规定,沱沱河、冈仁波齐、纳木那尼等,既是现实中存在的地理空间,又是诗人通过想象建构出来的幻想空间,形成了恢宏的诗性空间。他“石头”“水”等元素蕴含着姜耕玉对语言力度的呈现,每个元素都承载着较为深重的意义,也寄寓了他对生命精神的追寻。他希望借元素之力,对抗现实的疲软,重建诗性空间。姜耕玉的诗作也对诗坛有所启示:“力度”仍然应该是当下写作的重要追求。其三,姜耕玉也注意诗句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与节奏的控制,尤其是句号的使用,常使句子有戛然而止的感觉,在制造的空白中体现无限的意蕴。

辛北北(山东大学):
姜耕玉诗歌与“美文”的自我克服
读姜耕玉老师的诗,有久违之感。一方面,姜耕玉这些文本所集合的强烈抒情性,在近一二十年当代诗歌的风向转变中已相对少见;另一方面,他的诗很用心地在书写自然的维度上寻求诗学建设,这种自觉意识很重要,也很珍贵。
姜耕玉的诗在诗学建设方面的自觉,让我联想到新诗长久以来的“美文”现象。原本,美文是新文学以来散文领域的一个种类,可谓新文学自由表达的理想样态;然而在当代诗歌中,美文这一术语也经常被使用,且带有“贬义”的性质,如写自然的、修辞感过分凸显的、抒情饱和的、审美惯性的诗,就经常被视为美文。阅读姜诗,也并非没有此类感受,然而我认为,对姜诗的更准确评价,恰恰出自于跟反省前述“美文”之自相矛盾的同种逻辑:事实上,就新诗的发展史来看,视一首诗为美文,并不总是坏的评价,“美文”本身是一套诗学理念,其中既包含需要被批评的一般性美文,也内含一种自我超克的逻辑,即在写作中,基于语言工作本身,自我摆脱审美惯性,再度朝向更为崇高的“美”。这一点在不少诗歌文本中都能获证。同理,姜诗在书写自然的同时,由于不流于表面,也试图赋予其新的、整体的世界观,因而带来了“美文”自我超克的其中一种实践。

雷昭利(山东大学):
以自然书写抵达生命的“在场”
姜耕玉老师与自己所向往的西部、北部地区建立密切的精神联系,将行旅地点和场景融入诗歌中。这种地域性并非简单的自然主义,而是追求个体生命与边陲大地的灵魂对话为旨归,营造出具有生态审美特征的诗境空间。
在与自然对话的场景当中,是非常容易探寻到内心自我生命的一种本真的。姜耕玉也会因落日的那种孤寂雄浑之美想到人类与宇宙同衰那种渐渐流逝的美,与此同时,也蛰伏着一种暮年心境,但是自然反馈给他的美却让这种迟暮心态变得更加豁达。姜耕玉的诗歌中多出现方位向西的意象,并且大多都与一种静穆感、神圣感相伴相生,任何与“西”相关的意象仿佛成为了姜耕玉内在精神的象征。他对自然生态的忧思抒怀,对边地生态保护问题的关注,都指向生命的真实在场。
姜耕玉在自己的静穆中领悟出天地山川的大音无声,在深入自然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在西部广袤的山川草原中寻得主体心理的自由感受。这些描写西部场景的诗歌,真实体现了诗人将个体生命与自然重新联结与修复二者原本有些陌生关系的努力,从而让自己进入与自然万物相互关联的生态整体,实现诗人心目中关于道家物我合一、道法自然的美学追求。道家生态美学中最核心的就是自然之美,这种自然美往往是我们现代文明所造成的异化和内卷病症的良药。诗人的这些生态书写有利于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万物互相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同时也唤起读者对自然整体的审美感觉、体验,以及对美好世界的想象力。

赵思运(浙江传媒学院):
他的“积极后现代主义”拓展了西部生命体验的新向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牧、章德益、周涛、昌耀、沈苇、马丽华、刘亮程为代表的“新边塞诗”,以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和独特的创作风格成为文学史浓墨重彩的篇章。90年代以来,“新边塞诗”日益式微。在这种背景下,来讨论姜耕玉的《寂寥如岸》,就特别有意味。
姜耕玉的西部诗写则是独特的“这一个”。他的目标是双重的:既实现海德格尔所言——“物”中的诗性敞开,又获得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大卫·雷·格里芬所言的“在家园感”。他重新发现西部自身的“物性”,用心灵去倾听世界的寂静,用灵魂去融入原始的本真,召唤出“亲在感”和“在家园感”。海德格尔发出的叩问“人类从何处听到达到某物本性的呼唤?”姜耕玉在诗中给出了回答。“在家园感”的呈现与敞开,所揭示的诗人主体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经常构成饱满的张力:一方面,通过向上的“力的图示”烘托出一种值得仰视的神性存在和难以接近的敬畏感,另一方面,在灵魂里又幻化出天人合一的主客体充分交融的境界。
将姜耕玉的西部诗写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考察,很有意义。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流行的论调趋向于“消极后现代主义”,遮蔽了后现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强调文化同自然精神的创造性沟通融合。姜耕玉的诗歌让我们思考在后现代社会中如何构建新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明,如何去回应大卫·雷·格里芬的提问:“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之后,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对待人类社会?”“我们怎样才能保障人类以外的物种的权利?”在崇尚先锋与反叛、颠覆与解构的时代,姜耕玉着实在反向拓展着“积极后现代主义”的诗写空间。

姜耕玉(《寂寥如岸》作者):
首先,感谢诸位专家对拙诗集的批评,这对我以后创作注入了重要的营养剂。
最早在1998年,我第一次去内蒙古草原,写下的第一首西部诗《草原歌声》:“草原歌声/唱远了绿色/唱蓝了天空”,“我嗽一嗽嗓门儿/抖落半个世纪的叹息”,比较表面。《寂寥如岸》的灵感出自2004年暑期漂泊西藏,从藏东墨脱原始森林到藏西荒原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冈仁波齐神山,于陌生而神秘的自然中“生命和灵魂的亲近”自然而生,回归初始,回归本真,倾听“达到某物本性的呼唤”(海德格尔)。也是这次漂泊,有了对高山大川和自然生命的敬畏感。
同样,我对语言和诗也有了敬畏,不敢有半点虚假或矫揉做作。我吸取自己喜欢的诗人的经验,比如埃利蒂斯、聂鲁达、佩斯、W.S默温等,卞之琳、洛夫、昌耀、西川等,按自己的喜好和方式写诗,写对自己生命和灵魂有感应的诗。
我没有一举成名的才情,直至天命之年之后,写诗的脑子才得以“开化”。退休以后,似乎才到“巅峰”状态,只要有状态,我就不会停下诗笔。
原载于思想守夜人公众号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