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扩散的文化美学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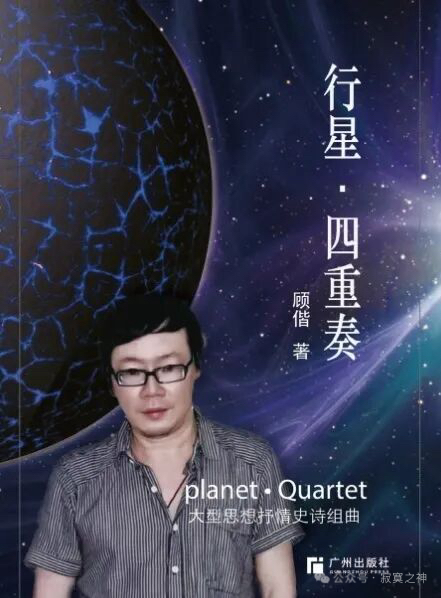
跨文化扩散的文化美学整合
——顾偕长诗《行星·四重奏》翻译札记
作者:林元跃
但凡论及《行星·四重奏》(广州出版社2024版)的跨文化扩散传播,无论是文化原型的纵向深入,还是延展比较的横向联系,都得先从笔者前期译作随笔《论一种终极美学的张力结构》所述诗意具有的概括力,作为相互关联人类与宇宙精神原型及神性感应的“前瞻性”补遗说起。即表现深度的价值体验,既具有内在性也具有超越性,其对人类命运精神危机的忧患,均是从文明困境中的灵感突围出发的。诗人顾偕醉心于他以悲悯的冷峻和情调昂扬的笔触,叩问着人类何以在宇宙中存在、文明何以对抗虚无的终极命题。作品语言层面已然实现了抒情性与思辨性的交融,并使冷峻的宇宙规律获得了诗性的温度,人类的命运的焦虑就此也升华为一种精神的觉醒。这种为长诗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启示,及其可贵的语言艺术革新与探索方面的先锋性实验,还构建了一个兼具生命温度与精神深度的诗性宇宙乐章,为读者点燃了诗与美能够传递人类于浩瀚宇宙中寻找存在坐标及文明航向的精神薪火,同样就像那种从事了文学创作40多年及构思了这部长诗30年不倦的诗歌精神,一直亦在创新的路上。“……不要怀疑星光时代/虚无的高歌环绕宇宙遗忘中还在燃烧的行星”
象征自己行星般燃烧的炽热将要影响全球化的当代情绪,作者便是这般对人文生存价值,赋予了新的巨大评判与同情。它关注人类在世界的日渐衰退、理想意义于挫败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它深化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更为读者提供了对人类未来和存在的深刻思考。尤其给于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为可贵的语言艺术革新及探索方面先锋性的实验!
美学家丁来先教授在《诗人的价值之根》中认为,真正的诗性语言能唤醒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哲思,诗人归根结底代表着人类的内在精神,诗人的价值和人类心灵的深层渴望有着密切的联系。“犹如永不降落的音乐/在浩茫星河潺潺流动/一种极端的宏伟保持着闪亮的梦境”。《行星·四重奏》作为“人类精神象征”的永恒性时空跨越的“不落音乐”,其“宏伟梦境”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创造与救赎如此长诗的价值使命,若星河般流动的诗歌语言重构现实,它已将宇宙星象规律,在“四重奏”里转化为了某种精神符号的扩散传播,甚至作为跨文化生存的精神档案,同时展现出了其诗集于全新而陌生的语境中,迸发出新的思考力与生命力。这种表现了文学人类学与当下宇宙观热点(文化原型的探索)的相互渗透,同样亦较好地形成了文化美学模型相互承载的扩散传播。另见丁教授的《诗意人类学》论说宇宙本身所蕴含的秩序、规律、和谐与神秘性。如同诗人用语言创造意境,属于文化形式的自然美具有自然特性与文化特性的某种交融与发挥,一样在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于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实,这些特性正是《行星·四重奏》划时代的辉光。即将创作理念促成审美意识形态的意象艺境,多形态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诗学科建设在当代美育中的价值。诚如荣格美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强调艺术作品是个体自我表达的途径。因此,符号与象征,其美学思想与艺术创作的关系,包括个体内心世界怎样的表达,以及阅读体验的主动参与,和突破传统界限等方面的影响而将如何实现一种创新性的审美期待,这对增强文化生态的重构与文化美学的新的生成尤为重要。
诗人顾偕一方面以深度整合的生态批评,进行着哲学思想与诗歌的互动;一方面又凭借跨时空诗歌精神的对话,如天问式的九章类比,形成中西方宇宙观与生命观的异质同构 。这种注重天人合一“内在超越”与神人分立“外在超越”的平衡,创造性地完美演绎了在“黑洞纪元”的演化,走向了更为辽远的星辰位移的诗之交响。“光年之外时间叫虚无/夜晚是所有生命的假日/晴空纵然是化石的镜像/影子在喧哗中实现了预言”。当这些意象一一转化为哲学思考的载体,宇宙的演化与人类的命运,便在诗人的终极关怀中熔于一炉了。而要实现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诗与思的博大与崇高”,并欲进行一次穿越概念黑洞的星际航行,则需要有“走向终结是一切诞生的绝对规律”的超前认识。否则宇宙潜能的循环隐喻,很难会在物质世界的剧烈变动与毁灭中重塑。
另一方面,该诗在对跨文化的美学关注及其文化现象的超越性、平等对话、乃至点面相济的横向延展等方面的比较,对文化审美中东西方难免的碰撞,亦都作出了多学科的整合。此种在诗歌创作上的努力,无疑是想在全球化语境下,在文明困境中甚而于文化差异中,寻找到一种诗性理性的平衡。亦即作者试图将一种文化自觉,在与全球化策略性跨文化对话时,能将自身持续的深悟与灵感顿悟,尤其能把“虚实相生”的东方“意境”,较为成功地切入到西方美学倾向“理性表现”的那些碰撞中。
《行星·四重奏》不同乐章的交响文化美学主体性,实质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为根本的。“一种极端的宏伟保持着闪亮的梦境/正向宇宙的花园,释放着”:“星辰之上/这里只有熔化与重生的形成/极限的人生与精神的旅行/荒芜内部全是生命的尽头/灯火不懂苦难的黑夜/你同大地的欲望恰好与此相反/宇宙的步履是人间岁月/再无时间的面具/磨损会慢慢布满所有星辰/星光曾是奇迹和预言”。诗人经过合并、分拆、增强、减弱等手法,形成一种文化新质,使长诗通过文学人类学视角,纵横构建了一个宏大而立体的诗宇宙艺术和哲学思想框架。这其实个以“天人合一的内在超越”为根本的跨媒介美学体系的基石和灵魂。“你看不到这空中的河流/早已有的宇宙的航程”,你会关联其不同乐章的交响或变奏着“一切都在继续不断变动中/在尘埃与尘埃之间锻造的万物骨骼,飘向星辰的火焰/已然漂浮在破灭中的宇宙/一切初始之物仿佛还在年轻地扩展” 。诗人从“一种边界的转译不是终点”,到时间深度整合中焕发出的本土文学观的特色与活力,这样的文化美学建构,为一种庞大史诗融合机制的支撑,同样亦较为充分地揭示中国文化生态,与之相适应的宇宙观在世界文化中的共生关系。一种虚实相生的意境以创新性表现,构建立了“全球视域-文化精神”的双向互动的美学方法论,足以用东方的诗歌品牌,将个体生命体验升华为民族的集体记忆,为世界提供一种重新审视宇宙的蓝图。
坚定的文化自觉源于创新性思考,而敢于向世界诗坛发出不同凡响的应战,自是需要诗人具备一种挑战名著的人类更大的勇气与责任。宇宙的最高法则和神圣根源永远存在于人之外、世界之外,时间与语言的终极奥秘——互动中的认知边界,本质便是人类认知能力与宇宙本质之间互动关系的基点,我们似乎惟有不断突破认知的边界,语言在“描述已知”与“创造新义”中继续不断推动思维进化,艺术在持续拓展中,才有可能出现重要的再造内容。包括像《行星·四重奏》这样的长诗,相信在跨文化星辰中,有朝一日也会嘹亮地发光和发声。
以宇宙诗学为魂的跨文化坐标,在"太阳系-黑洞-花园"的螺旋上升中彰显"星尘生命共同体",是创新性抒情长诗的灵魂气度,更是造就了大型史诗的新纪元。人类对宇宙的诗意表达,既可以像《行星·四重奏》那样,是一场冷静而恢弘的哲学远征;也可以像《太阳石》那样,是一场热烈而迷幻的生命狂欢。它们如同宇宙中的双星系统,在美学引力的相互作用下,将会共同照亮人类精神的浩瀚与深邃。但是,前者在“星辰之上/ 通往宇宙的尽头/ 意义是尘埃闪亮的聚集……”既承续又拓展了但丁《神曲》的宏大叙事与屈原《天问》的精神宇宙,又在跨文化重生的宇宙共同体伦理中,完成了超验意象的诗学革命!使之"极端的宏伟释放闪亮梦境",在悲悯中促使浪漫主义飞跃至星际多维视角,进而于跨文化的超越与创新中实现一种完美的表达。诗歌巨著艾略特的《荒原》和与之媲美的600行长诗《太阳石》,就是在形制规模、主题拓展、诗学创新等方面,都具有了世界级艺术翘楚的水准。同样,两者均属超现实主义诗人所具有东方神秘主义音乐美的光辉,在主题迭代的螺旋上升与交响乐思维的文学移植的对比中,语言更富于暗示性和反射性——以此亦折射出了超验的“动态平衡”,作用于文化生态与哲思诗美的虚实相生。
顾偕的《行星·四重奏》,就是勇于整合文化美学、强调文化动态过程的互动性与融合性,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世界的终极性觉醒和协调,在文化差异与共同体之间寻找平衡的一种诗歌实践典范。在宇宙时空漩涡断裂处,重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精神连接,尤其想在文化自觉与全球化策略跨文化对话中,做到做好与主体性文化价值的主导作用,它必须呈示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撑:
(一)中国宇宙观有着气化流动时空合一的特殊性,从文化精神去理解其整体结构,一般较为吻合大文化视野的整体性观照,所以亦可称为“文化美学”宇宙本体的虚灵化、个性的自觉以及审美体系的扩大和演进。在《行星·四重奏》看来,一个无限宇宙中,审美不能单从政治-等级-伦理等社会方面去寻找依据,而是要从美本身去获得体悟和感觉,应验神韵,进而正面回答为什么说这是一部具有文化美学特征的质疑。其显著标志是,中国美学是带着中国天下观特点的美学,就如整个诗歌艺术亦应反映天地之心、万物之情,对称于宇宙的时世灵魂。所以该长诗以其星尘、生命、引力与光,谱写着一首无声而壮丽的史诗,既不是纯粹物理的客观属性,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臆想,而是自然的客观特性与人类文化特性在宇宙中不断的相遇,诸多自然元素有机对话所融合气化的一种诗性的璀璨共鸣。
(二)诗歌艺术是文化的抽象和灵魂。诗歌几乎一直是神圣的特殊社会意识形态,并以其特殊方式反映和掌握着世界。诗歌通过个人的创造力将宇宙物质能量转化至现实世界,这种转化过程,本身就涉及对现实的重新解读和再创造。所以,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其感性与理性相结合,以及形象性与象征性的表达,文化精神或生态批评等哲学思想的融合,目的在于试图以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与人类情感的普遍性,展示自己凝结于诗美的探索,并以意象张力之类通过扩散从而影响世界。
(三)顾偕的《行星·四重奏》以先知先觉的使命感,挑战西方现代主义中孤立、异化的自我观念,作品提供了一种通过“爱”与“诗”的瞬间启示,反射了一种能与永恒性抵达与融合的可能。在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的现代性进程中,这类长诗结构和审美文化联系的一体化形态的聚光、博识与共建、文化类型的“整合”及与自然宇宙的撞击和共鸣,都较为意外和透彻地揭示出中国文化生态与之相适应的宇宙观。即把理论与现实的家、国、天下、宇宙整体的四重关联,统合在审美文化的诗性一体中加以扩散和传播。
(四)用文化美学整合长诗跨文化的扩散传播,还得着意于翻译这样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手段。而诗歌翻译自古就是情感、美学信息的跨文化扩散的必经之路。由于中西文化审美差异,尽管必然会阻碍两个人群相同审美体验的产生,影响译介效果,但在诗歌翻译的种种传达中,文化传播美学却依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引作用。诗歌意象承载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和特定文化内涵的客观物象,所以当源文化中的意象在转译文化中不存在、或具有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时,往往就会使读者对译作产生歧义。因此当诗歌把意象作为一种特定方式的价值诉求时,就迫切需要我们以一种创造性转化达至艺术的最高境界,而不影响读者对诗歌作为整体艺术品的重新审美体验。译者必须深刻理解原诗意象的精髓,在目标语中寻找或创造一个新的、具有同等美学效果和情感冲击力的表达方式,这不仅仅是大容量的外在替换(其他语言文字),还是能使一种跨文化的流畅性,以意象传递独特文化内涵的一种可译性艺术的再创造,说穿了也就是对某种意象跨文化超验力量的传递与重构。譬如在《行星·四重奏》里,作者的哲学沉思与叩问,惊愕或憧憬、意象的文化摆渡中对当下与未来的辨识,诗人都会努力在“归化”与“异化”之间,让将来的译者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甚至提前激活所有具象性美感,使原诗亦能遇上知音,让译作成为两种文化的桥梁,使中西方读者均可于作品中,获得与宇宙对称的灵魂。构建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巨峰,并在宇宙神奇的永恒意识面前,最终能够从容地成为诗歌精神的创新者,无疑这对中国诗人还是一部伟大作品的译者,一样都是任务艰巨的。
综上四个方面看《行星·四重奏》文化美学产生的基础,是诗人与人类在宇宙相遇:“钥匙贴近门的呼吸/答案在房内”对世界作出文化美学整合性的回答。因此,怎样把时空合一的虚实相生,继续导向宇宙的虚灵化,永远还是哲学内核内敛的宇宙能量精神升华的起点。在时空飘零,浮悬的生命于永恒中人类超越性的终极追问,不只是对应现实体验的潜在跨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那种可将个人无意识的触动力与人类意识互动进行对话的文明意识的整合,想来更是个人的“独立宇宙”,朝无限创造力价值发展的更大精神引擎。
2025、11、16初稿于自贡

作者简介:林元跃,四川轻化工大学主任编辑,著有诗集《意象神雕》、学术专著《大学精神的培育创新》以及大学写作、书法教材多部。多篇小说、文旅、文化等论文和诗文联赋及译作在全国获奖。曾获上海“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奖、首届全球诗酒文化论文二等奖、山东沂蒙精神评论奖、黄鹤楼诗会诗论奖、深圳大湾区诗歌奖、四川疫情防控诗歌一等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