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缓起伏中的叠嶂峰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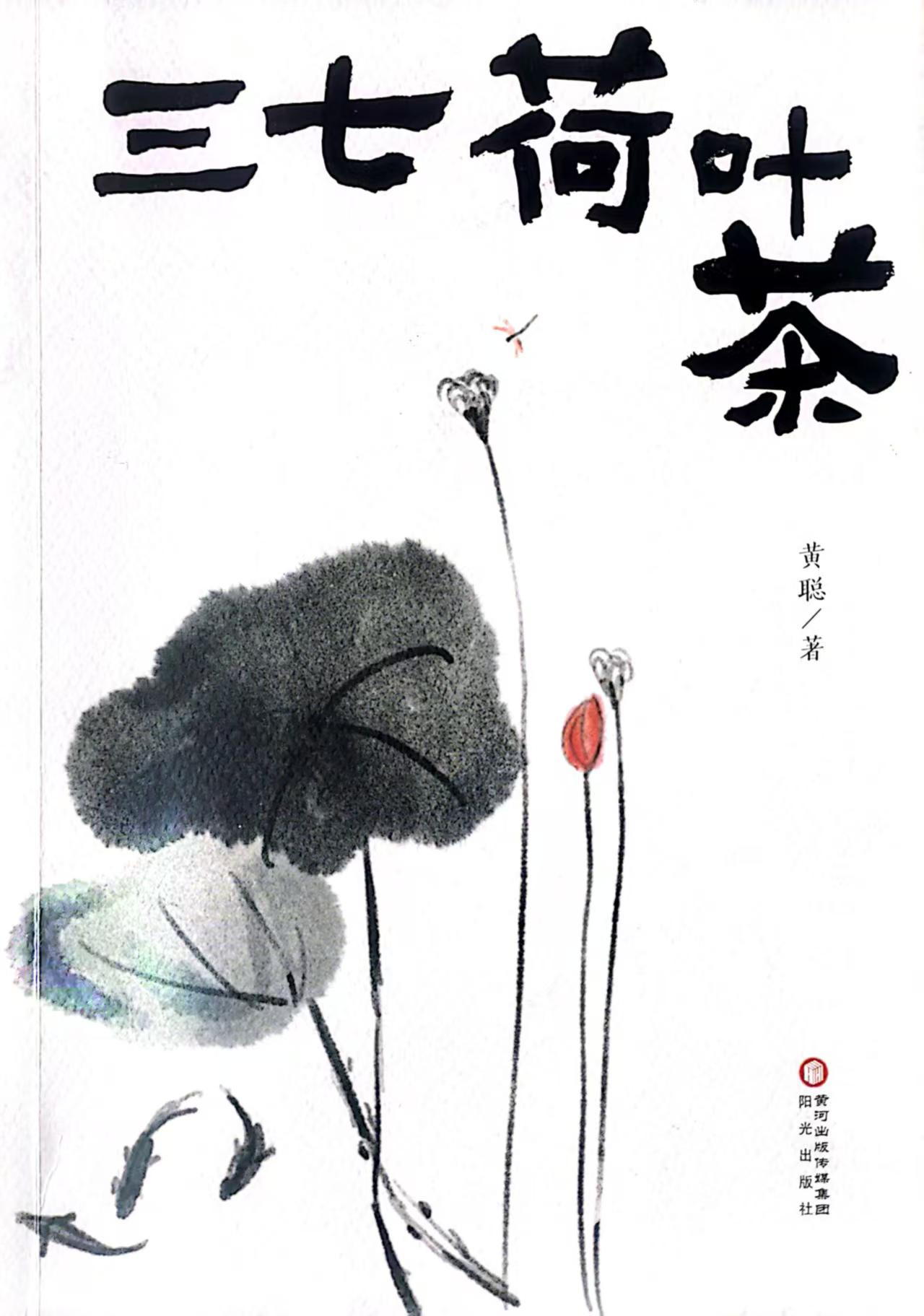
舒缓起伏中的叠嶂峰峦
——读黄聪小说集《三七荷叶茶》
万治友
没接触到这本小说集的时候,就有阿右旗的朋友说她被黄聪的小说集《三七荷叶茶》看哭了好多次。我当时还有些疑惑,黄聪的中短篇小说我也看过不少,其风格、架构、语言不可谓不熟悉,其中的有些篇章确实能击中内心的痛点,让人读罢感觉到隐隐的痛,但要说能把自己看哭,还是觉得有些言过其实。
等看过几遍后,就有了与朋友相同的感觉。随着阅读的深入,真正把小说的精髓看到心里才发现,小说集中的某些因子确实能在自己心里扎下根,与自己原有的某些记忆和经历混合,产生极度深刻的共情,触动内心最柔弱的部分,让人泪水盈眶。
小说集共八个短篇,正如大部分作家那样,黄聪的小说也有很明显的地域特点,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西北部沙漠边缘的沙漠和小镇,写的都是普通人家的普通故事。如《月香》中,作者围绕女主角月香一次采沙葱的经历,从早上出门拦车到风雨中去寻找躲雨的那个山崖和洞窟,时间跨度只有短短一天。
采沙葱对当地人来说再平常不过了,过去牧区吃不到新鲜蔬菜,沙葱就是日常最重要的菜蔬,现在交通便捷了,加上大部分人都进城居住了,但沙葱仍然是本地人不可割舍的情怀,不少人不惜携家带口开车几十公里到牧区去追寻记忆中的那种味道。但作者能从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琐碎中提炼出一篇故事,构思出一篇小说,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作者并没有把着笔的重点放在采沙葱上,而是用大量笔墨描写主人公在路边一次次拦车失败的经历和暴风雨中无助和心理抗争。从一开始的“雨,悄无声息地来了”,到“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沙漠里已经看不见地面了”。而主人公月香也从一开始“蜷在冬青树下”到“山洪下来把她冲进了洪沟中”,故事自此从平铺直叙转入跌宕起伏情节之中,这样的转折虽然急速猛烈但并不突兀。中间通过插叙方式对月香一家家庭变故的介绍,既让读者明白了故事的背景又为故事走向高潮做了情感铺垫,成为整个故事不可或缺又无缝衔接的重要一环。也因为对这些背景的介绍才使这篇小说有了可读性,有了创作最基础的土壤。小说的结尾又回到了公路拦车上面,这是对小说开头的回应,也是对结尾的又一次铺垫。月香拦车未果后又想起了“那个山崖和那几个洞窟”,路上“视野忽然开阔起来,月香面前出现了一条平坦的大道,前方闪耀着家里才有的温馨的灯光”。这是小说主人公内心泛起的希望之光,更是作者为整篇小说设计的前后呼应的结尾方式。其手法我们并不陌生,但其中充满着的人性关怀,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预期。
小说集中所讲的故事,打着深深的时代印记,《班驼》就是其中的一篇。小时候家里去苏木打粮,也是要集中起家里的骑乘一次驮够一年的口粮。后来修了公路后开通到旗里的班车,人们的出行才方便了起来。而小孩们上学也是件天大的事,因为困难太多,所以辍学的很多,能坚持上完学的寥寥无几,这要靠父母的决心和远见。而小说主人公的父母显然是具备这种决心和远见者的其中之一。小说的前半部分平铺直叙,几乎没有波澜,后半部分突然出现转折,这也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就在班驼回家途中的最后一天,“额尔登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羊皮袄不见了”,这真是要命,谁都能想到大冬天在沙漠中丢了皮袄意味着什么。这时候作为班驼班头的阿穆尔把自己的皮大氅给了额尔登,而自己“上身只剩下一件褪了色的红绒衣”。暴风雪中驼队无法前行,只能就地露宿,阿穆尔安排好驼队和所有孩子,“咬着牙关安慰我们”。小孩们睡着了,“似乎还做了一个梦”,但阿穆尔在试图找点干芦苇取火的路上跌在了芦苇丛中再也没有起来。他的身体被雪覆盖,融入了沙漠,而灵魂交给了长生天。
读完整部集子,可以发现收录的八篇小说都带着些许忧伤,或多或少,或浅或深,或隐约或显现。可能有人说这样的基调过于昏暗和低沉,但我反而觉得更能衬托出主人公心灵中那种深沉的爱意、炽热的内心和粗犷豪迈的情怀。而所有这些,酿就了沙漠戈壁间人们与自然既相争又相融,既相恨又相爱、既想离开又万分不舍的情感。
整个小集中的爱情几乎都带着几份苦涩。《班驼》中阿穆尔与巴依勒,两情相依,但因为中间隔着个巴格达(主人公的父亲),所以一直不能入愿。而那条从供销社凑钱买下的红围巾最终没能亲自交到巴依勒手上。在阿穆尔的葬礼上,巴依勒“胸前搭着一条鲜艳的红围巾,仿佛跳跃的火焰,在洁白的雪地里飞舞”。其实在这篇小说里,爱情并不是主线,真正以爱情为主线的是另一篇小说《草儿青草儿黄》。
这篇小说的结构非常新颖,通过几个角色分别叙述的方式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当地牧民家的女子琪琪格与部队牲畜班班长张振山相恋相爱还生下孩子的故事。张振山由此违反了部队纪律,从此两人天各一方,成为相隔千里的鸳鸯。两人的心里都装着对方,都在爱的痛苦中煎熬,却阴差阳错地彼此错过,直到最后张振山被战友找了回来父子相聚。这是喜庆的结局么?其实不是,反而因为这样的结局更加深了爱情的悲情色彩。读过几遍后,再读到此处就不忍再读,生怕自己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而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小说里的爱情是悲壮的,但这更突出了另一个重要人物浜提来的人格魅力。我甚至有些犹豫,是不是应该把主角的地位给他。因为小说的主线自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浜提来,他是琪琪格年青时的狂热追求者,甚至在张振山离开后,只要琪琪格愿意,他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圆满的家庭。在不能如愿的情况下,浜提来一直照顾着这一对母子,琪琪格离世后一直照顾巴图础鲁上了大学,考上公务员后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但他一生都有一个心结,就是因为张振山的背信弃义给琪琪格带来的伤害。“就是等他算账,拼上我这条命,我也弄死他”。最终在张振山战友的撮合之下终于握住了张振山伸来过的手。但他真的释怀了么?我看也未必,这么多年心里的结哪能因为暴揍了对方一顿而完全消弭?只不过他的胸怀里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装下了而已。
而我想说,这才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生生不息的源头吧。能装下沙漠戈壁的荒凉,能装下千里无人烟的孤寂,就能装得下天地,装得下所有的人情事故。这是这里的人们朴实、善良、正直的根本,是真正的自然之心、赤子之心。而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正是对纯粹人性的赞美,以及这种根植于自然、未被世俗侵蚀的本珍品质。
除了对人性自然之美的赞扬,作品中表现出的万物和谐共生的理念也值得关注。比如《猎狐》中,满达呼打死公狐之后,又发现了母狐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小狐狸。名叫大黑的狗咬死母狐后又连续咬死几个小狐狸,满达呼想叫住大黑,但大黑已经杀红了眼,就在它扑向最后一只小狐狸的时候,满达呼的枪响了,而这次倒下的不是小狐狸,而是大黑。“大黑叼着小狐狸栽倒在地上,眼睛看着主人,慢慢暗淡了”。这是主人公或者说是作者最后时刻的心生怜悯,还是对小狐狸生命的惋惜?其实作者在文中已经交待得很清楚了。满达呼看到小狐狸们争吃着弥留之际的母狐最后一滴奶水的时候,“记起中午乌兰图雅的眼泪,都是母亲啊,咋就这么残忍?”。这是作者在问自己的内心么,还是向整个社会、 整个自然的呼唤?
还有一篇是《骆驼泪》,讲述了主人公哈琳娜收养了一只失去母亲、断了一条腿的小驼羔,最后在嘉木苏喇嘛和身边朋友的劝说下,为驼羔在牧区找到了新妈妈。整篇小说围绕驼羔的喂养、医治、送走,到最后与母驼的相互接纳,一帧帧感人肺腑的画面具有很强的带入感。其中最触动我的是嘉木苏喇嘛的那句话“万物皆有道,牲畜不能一直养在家里,从哪里来就往哪里去吧。”小说中另外两个人傲云和莫日根都表达了相同的理念。这其实就是草原上人们最朴素的生态理念,是千百年来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文基础。
有一篇小说不能不提,就是《三七荷叶茶》,把这个篇名作为整本小说集的书名,可见这篇小说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这是集子中唯一一篇离开了牧区,把着眼点放在城镇的小说。与作者聊天时,曾说起这篇小说的渊源。据他讲,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次他到朋友茶庄,朋友为他沏的三七和荷叶泡的茶。这两种本是中药的材料混合在一起泡出的味道令他顿生灵感,一篇小说应运而生。小说主人公歆玉虽然依托于企业老板徐总开了茶庄,但当决定徐总命运的邱三决定把歆玉追到手,“让老徐吐血本”时,歆玉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商业交换的工具,而是“砍了老徐一刀”,自此离开了小镇,不知去向。
与歆玉一样生活在社会的角落,但仍保持着自己尊严和做人原则是这部小说集中主人公的本色,除了以上提到的人物外,《苁蓉花》中的娜仁高娃、《最后一个土匪中的》老嘎瓦等等都是。尤其是老嘎瓦,虽然自己杀了土匪,但被人误解了一辈子,还坐了两次牢,这不是命运在捉弄人么,但老嘎瓦把这一切都装在了自己的心里,默默承受了一辈子。
无论是暗香、歆玉,还是老嘎瓦、阿穆尔,小说集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社会上的小角色,都是普罗大众中最普遍的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甘于命运,或虽处底层但责任感十足。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们的社会不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组织成么,他们在作者眼中的位置不就是不屈不挠的脊梁和精神么。
作者简介:万治友,笔名:之友、遥远。中国诗歌学会、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梦中的歌谣》。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