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诗歌概念”地域书写的再界定
“北京诗歌概念”地域书写的再界定
——以叶延滨、耿占春、卞之琳、沈浩波、树才、诗豪天诗歌的北京书写为例
●杨青雲(《北京诗歌概念书系》特邀撰稿人)
在当代中国诗歌的坐标系中,北京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精神地标”。它既是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历史容器,又是现代文明与传统基因激烈碰撞的前沿场域;既是国家意志的象征空间,又是无数个体生命的栖居之地。当“地域书写”成为诗歌研究的重要维度,北京诗歌的特殊性便愈发凸显——它不仅是对一座城市的景观描摹与经验记录,更是民族文化记忆、现代性焦虑与精神主体性建构的集中呈现。本文以叶延滨、耿占春、卞之琳、沈浩波、树才、诗豪天的诗歌为核心文本,从“空间表征—精神投射—语言建构”三重维度考辩北京诗歌概念地域书写的内涵边界,重点探讨其如何以地域为锚点强化民族文化主体性,并为汉语言的现代性转型提供诗性支撑。
在进入具体文本分析前,必须先厘清“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核心界定——它并非简单以“北京”为题材的诗歌集合,而是以北京的地理空间、文化肌理、历史记忆、社会生态为载体,实现个体经验与公共精神、地域特质与民族共性、传统基因与现代意识交融的诗歌创作。其界定需紧扣三个维度:
北京的地域空间具有天然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永定门、钟鼓楼、故宫、中轴线等承载着皇家气象与历史厚重的“传统空间”;另一方面是CBD、城中村、地铁线路、移民社区等彰显着现代节奏与生存压力的“现代空间”。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正是通过对这些空间的诗性转化,将物理空间升华为文化空间。如诗豪天《北京中轴线》中“永定门的垛口衔住第一缕晨曦/七百多年的光阴从砖缝里簌簌落下来”,并非单纯描写永定门的建筑形态,而是将其转化为历史时间的“具象载体”;沈浩波《雨中抒情》里“阜成门的空气指数/每天吓我一跳”,则以阜成门这一具体地点为切入点,折射出北京现代都市的生态焦虑与生存困境。这种“空间诗化”,是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基础前提。
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身份,使其地域书写天然具有“超越性”——个体在这座城市中的生命体验,往往能折射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叶延滨《中国》中“不,可尊敬的小姐,对于我的祖国,长城——/只不过是民族肌肤上一道青筋/只不过是历史额头上一条皱纹”,看似是对“长城”这一传统符号的解构,实则是通过对民族象征的重新认知,建构现代中国的精神主体性。这种“个体发声—民族回响”的逻辑,同样体现在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中:树才《安宁》对住宅小区日常的凝视,暗含着对现代都市人精神归处的思考;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对生命困境的追问,折射出转型期中国人的存在焦虑。可以说,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始终在“个体”与“民族”的张力中寻找精神共鸣点。
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终极价值,在于为民族语言提供新的表达可能。北京方言(如儿化音、京腔词汇)虽可为诗歌增添地域色彩,但北京诗歌的语言贡献远不止于此——它通过将北京的历史语境、文化特质融入汉语言表达,让民族语言既扎根传统又贴近现代。卞之琳《鱼化石》中“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以极简的语言承载着时空错位的哲思,这种语言张力的营造,与北京“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文化特质高度契合;诗豪天《北京中轴线》将“九三大阅兵”“申遗成功”等现代事件与“太庙柏枝”“社稷坛五色土”等传统意象并置,实现了语言的“历史纵深”与“当下在场”的统一。这种语言实践,让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超越了“地域本位”,成为民族语言现代性建构的重要路径。
北京诗歌概念文本解构六位诗人的北京书写与主体性建构
六位诗人的创作横跨近百年(卞之琳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沈浩波、树才为当代诗人),其北京书写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但核心都指向“地域特质与民族精神的融合”,尤其是通过强化北京地域的辉煌主体性,为民族语言注入新的生命力。
(一)叶延滨《中国》:民族符号的重构与北京精神的隐性呼应
叶延滨的《中国》虽未直接描写北京,但诗中对“长城”的解构与“中国”意象的重塑,与北京作为“民族精神枢纽”的特质形成隐性呼应。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其地理起点虽不在北京,但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都城,始终是长城所代表的“防御文化”与“民族认同”的核心承载地。诗中“年轻的我——高昂的头,明亮的眼,刚毅的体魄”所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与北京从“帝王之都”向“现代首都”的转型轨迹高度一致。
这种呼应的深层意义在于:叶延滨通过解构传统民族符号(长城),打破了对“中国”的刻板认知,而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正是需要以这种“解构—重构”的逻辑,打破对北京“皇家气派”的单一想象,挖掘其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中国》所彰显的“民族主体性”,为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提供了精神坐标——北京的辉煌,不应仅仅是历史的辉煌,更应是现代中国精神的辉煌。
(二)卞之琳《鱼化石》:时空错位中的文化张力与北京语境适配
卞之琳的《鱼化石》创作于1936年,虽无明确的北京指向,但诗中“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所体现的“融合与疏离”“存在与消亡”的辩证关系,与北京的文化语境高度适配。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正处于“传统帝制终结”与“现代文明涌入”的转型期:故宫的红墙与胡同的灰瓦间,渗透着新旧文化的碰撞;文人的坚守与西方思潮的冲击,构成了复杂的精神图景。《鱼化石》中“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的“时空凝固感”,恰是这种文化转型期的诗意表达——旧的文化形态虽已“远去”,却以另一种方式(如鱼化石般)沉淀为民族文化的基因。
从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角度看,《鱼化石》提供了一种“间接书写”的范式:不必直接描摹北京的景观,只需捕捉与北京文化特质同构的精神内核,便能实现与地域的深层对话。这种书写方式,拓展了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边界,使其不再局限于“题材绑定”,而是走向“精神同构”。
(三)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生命困境的追问与北京的历史重量
耿占春的《当一个人老了》以哲性笔触书写生命的荒诞与困惑:“当一个人老了,才发现他是自己的赝品/他模仿了一个镜中人/而镜子正在模糊”。这种对“自我存在”的追问,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重量”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北京承载着太多的历史记忆,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仿佛在“历史的镜子”中寻找自我,却又时常陷入“镜中模糊”的困境。胡同里的老人见证了城市的变迁,却可能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感到自我迷失;年轻的北漂者追逐梦想,却可能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失去方向。
诗中“他的自我还没诞生”的焦虑,正是北京现代性转型中个体精神状态的缩影。耿占春的书写,将北京的“历史重量”转化为个体的“精神压力”,又通过对这种压力的追问,触及了民族文化中“自我认知”的深层命题。这种“以个体生命观照地域精神”的方式,让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更具人文深度。
(四)沈浩波《雨中抒情》:移民视角下的地域认同与民族情感
沈浩波的《雨中抒情》以“北漂”的移民视角,撕开了北京“辉煌”背后的生存真相:“我已习惯了在尘土中奔走/风沙袭击着我的眼睛”“我竟无端地想起远在故乡的父母/呵,白发的双亲,你们可知道,远在北京的儿子此刻的心情”。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它打破了北京书写中“宏大叙事”的垄断,以个体的“异乡感”与“乡愁”,建构了更真实的地域认同。
北京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据统计2023年北京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户籍人口超过800万。这些“移民”的存在,让北京的地域特质中天然包含“疏离与融合”的矛盾。《雨中抒情》中“失去了我的南方/失去了我的故乡/失去了故乡连绵的雨水”的失落,与“就将留居京城”的选择,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而这种个体层面的“地域认同困境”,又折射出整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根脉焦虑”——当无数人离开故乡涌向大都市,如何在“现代”与“传统”“异乡”与“故土”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命题。
沈浩波的书写,让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从“宏大叙事”落地到“个体经验”,既展现了北京的“包容性”与“残酷性”,又通过个体的情感共鸣,强化了民族情感的凝聚力。这种“接地气”的地域书写,让北京的“辉煌主体性”不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充满人间烟火的生命体验。
(五)树才《安宁》:日常景观的诗化与北京的精神归处
与沈浩波的“焦虑”形成对比,树才的《安宁》聚焦于北京的日常景观:“汽车开走了停车场空荡荡的安宁/儿童们奔跑奶奶们闲聊的安宁/我想写出这风中的清亮的安宁/草茎颤动着咝咝响的安宁”。这首诗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北京现代化进程中“被忽略的宁静”,为北京的地域书写提供了“温情视角”。
北京不仅有CBD的繁华、地铁的拥挤,更有住宅小区的闲适、街头巷尾的烟火。树才的书写,打破了对北京“快节奏”“高压力”的刻板印象,挖掘出地域空间中的“精神归处”。诗中“占据我全身心的,就是这”的笃定,既是对“安宁”的珍视,也是对现代都市人精神需求的回应——在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喧嚣中,北京依然为个体保留着“诗意栖居”的可能。
这种书写的意义在于,它让北京的“辉煌主体性”更具温度:北京的辉煌,不仅在于历史的厚重、现代的繁华,更在于它能为每一个生命提供“安宁”的栖居之地。这种“日常诗化”的实践,丰富了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情感维度,也让民族语言的表达更贴近生活本真。
(六)诗豪天《北京中轴线》地域符号的整合与民族精神的具象化
诗豪天的《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集大成之作。诗人以中轴线为线索,将永定门、钟鼓楼、万宁桥、故宫、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等核心地域符号串联起来,构建了一幅“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北京精神图谱:“永定门的垛口衔住第一缕晨曦/七百多年的光阴从砖缝里簌簌落下来”“天安门的旗杆直插云端/红旗展开时像一片燃烧的霞”“北京中轴线是一根穿线的针/把南与北/古与今/都串在北京诗歌的上面”。
《北京中轴线》以中轴线为诗性锚点,将北京七百年的历史厚重、当代的时代气象与《东方红》的精神隐喻熔于一炉,既是北京诗歌地域书写的典范之作,更以其独特的诗学建构,树立起北京诗歌精神高度的旗帜。这首北京诗歌跳出了单纯的景观描摹,让中轴线成为串联古今、勾连个体与民族的精神纽带,其对北京诗歌概念的诠释与拓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价值。北京中轴线不是简单的地理坐标,而是北京城市文化的“脊梁”,诗豪天精准抓住这一核心意象,让诗歌从一开始就扎根于北京的地域基因。这首诗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北京的“地域符号”转化为“民族精神符号”:中轴线不仅是北京的地理脊梁,更是民族文化“南北贯通、古今传承”的象征;九三大阅兵、申遗成功等现代事件与太庙祭祖、社稷坛五色土等传统意象的并置,彰显了民族精神的“延续性”与“时代性”。诗中“每一个字/都带着古城青砖的厚重/瓦的沧桑/和人的温度”,正是北京“辉煌主体性”的直接表达,这种主体性,既扎根于历史的厚重,又彰显着现代的活力。
《东方红》的隐喻是《北京中轴线》的诗学灵魂,它为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注入了鲜明的精神底色,实现了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深度共鸣。社稷坛的描写是这一隐喻的集中体现:“社稷坛的五色土沉默着/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砌成大地的五脏/也砌成《东方红》歌声的声声嘹亮”,五色土是中国古代对土地的认知与敬畏,代表着东、南、西、北、中五方疆域,是民族生存的根基;而《东方红》作为从陕北传唱至全国的革命歌曲,是人民对领袖、对新中国的赞颂,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诗人将五色土与《东方红》并置,意味着北京诗歌的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同根同源,地域书写的内核正是民族文化的传承。
“古人们把对土地的敬畏捏进泥土里/让五谷的香从土里钻出来”,这句看似朴素的描写,实则暗含着“土地与人民”的关系:古人对土地的敬畏,本质上是对生存的敬畏、对人民的重视;而《东方红》的核心精神,正是“为人民谋幸福”,这种内在逻辑的契合,让《东方红》的隐喻不是生硬的植入,而是与地域文化自然融合。“歌吟了千年的《东方红》/比北京诗歌的红/更红/更鲜艳”,这里的“红”是精神的颜色:北京诗歌的“红”可能是故宫红墙的红、红旗的红,而《东方红》的“红”是革命的红、人民的红、信仰的红,它更鲜艳、更有力量,因为它承载着民族从苦难到辉煌的奋斗史,是北京诗歌地域书写中最厚重的精神底色。
尤为重要的是,《北京中轴线》与叶延滨《中国》形成了“相映成趣”的呼应:《中国》通过解构传统符号建构现代民族精神,《北京中轴线》则通过整合地域符号具象化民族精神;前者是“抽象到具体”的升华,后者是“具体到抽象”的提炼,二者共同指向“民族精神主体性”的建构,也为北京诗歌概念的命名提供了核心文本支撑。
北京诗歌概念理论建构的命名逻辑与语言贡献
基于上述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北京诗歌”概念的命名逻辑,并厘清其对民族语言现代性的贡献。这一概念的成立,并非基于“题材地域化”的简单归类,而是基于“精神地域化”与“语言地域化”的双重支撑。
(一)北京诗歌命名逻辑以“地域精神”为核心的三重统一
北京诗歌概念的命名,需实现“三重统一”:
1. 历史与现代的统一:如《北京中轴线》所示,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必须扎根历史(永定门、故宫等传统符号),又直面现代(九三大阅兵、都市生存等现代议题),在历史与现代的对话中彰显地域精神的延续性。
2. 个体与民族的统一:如沈浩波《雨中抒情》、叶延滨《中国》所体现的,北京诗歌需以个体经验为切入点,通过个体的情感共鸣与精神追问,折射民族的集体意识与精神需求。
3. 空间与精神的统一:如树才《安宁》、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所实践的,北京诗歌需将物理空间(住宅小区、胡同街巷)转化为精神空间,实现地域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同构。
这三重统一的核心,是“地域精神”的提炼——北京诗歌的本质,是“以北京为载体的民族精神诗化表达”。只有紧扣这一核心,“北京诗歌”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学术价值与诗学意义的独立概念。
(二)北京诗歌语言贡献为民族语言注入“地域基因”与“时代活力”
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对民族语言现代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1. 地域基因的融入:通过将北京的历史语境、文化特质、生活经验融入语言表达,让民族语言更具“文化厚度”。如诗豪天对中轴线、五色土等地域符号的诗化运用,丰富了民族语言的意象体系;沈浩波对“阜成门空气指数”“工体球场”等现代地域经验的书写,让民族语言更贴近现代生活。
2. 表达范式的创新: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北京诗歌探索出了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如卞之琳《鱼化石》的“哲性隐喻”,将抽象的时空思考转化为具象的诗歌意象;叶延滨《中国》的“符号解构”,打破了传统民族符号的固化表达;树才《安宁》的“日常诗化”,让平凡的生活场景成为诗意的载体。这些创新,为民族语言的现代性转型提供了诗性范例。
正如题目所强调的,北京诗歌“强化北京书写的辉煌主体性”,其本质是通过地域书写强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的强化,最终会“进入我们汉语言的血液中”,让民族语言在扎根地域文化的基础上,更具生命力与影响力。
从卞之琳的《鱼化石》到诗豪天的《北京中轴线》,从叶延滨的《中国》到沈浩波的《雨中抒情》,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始终在“历史与现代”“个体与民族”“空间与精神”的张力中寻找平衡,最终建构起以“辉煌主体性”为核心的地域诗学。这种诗学,不仅是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诗意记录,更是对民族精神的镜像呈现——北京的历史厚重,是民族文化积淀的缩影;北京的现代转型,是民族复兴的见证;北京的个体悲欢,是民族情感的共鸣。
“北京诗歌”概念的界定与命名,不仅为诗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地域书写对民族语言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当诗歌扎根于具体的地域文化,其语言表达才会有坚实的文化根基;当地域书写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其诗学价值才会有更广阔的辐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诗歌的地域书写,既是“北京的”,也是“民族的”;既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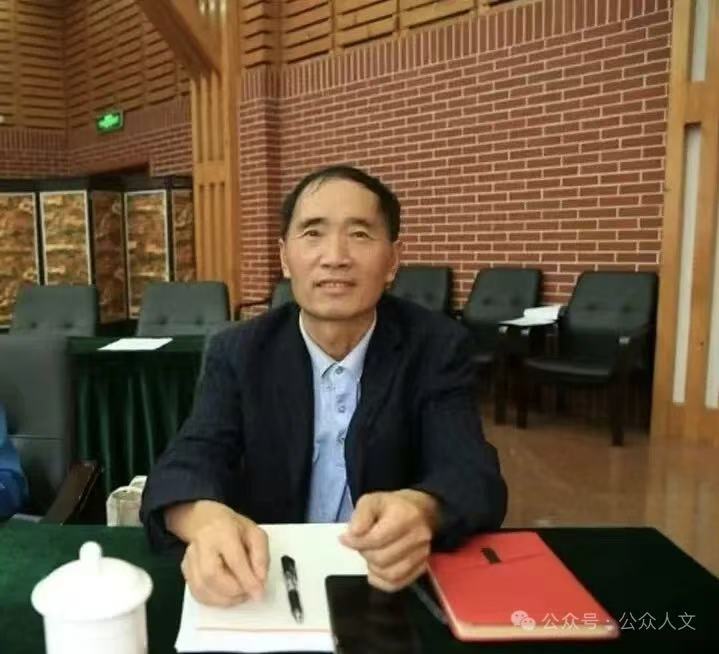 杨青雲 近照
杨青雲 近照
【作者简介】杨青云,曾用名杨晓胜,笔名梅雪、汝愚等。常驻北京。著有《范曾论》《范曾新传》《孔祥敬诗论》《周恩来研究》《范曾诗魂书骨美学思想窥探》《贾平凹美术论》《李德哲美术论》《北京虎王马新华新论》《忽培元浅论》《王阔海新汉画初探》《北京诗歌概念书系上部》《樱花结》长篇小说等。现为范曾研究会会长,北京周馆筹秘书长兼《周公研究》新媒体总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