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麦浪舞 群像如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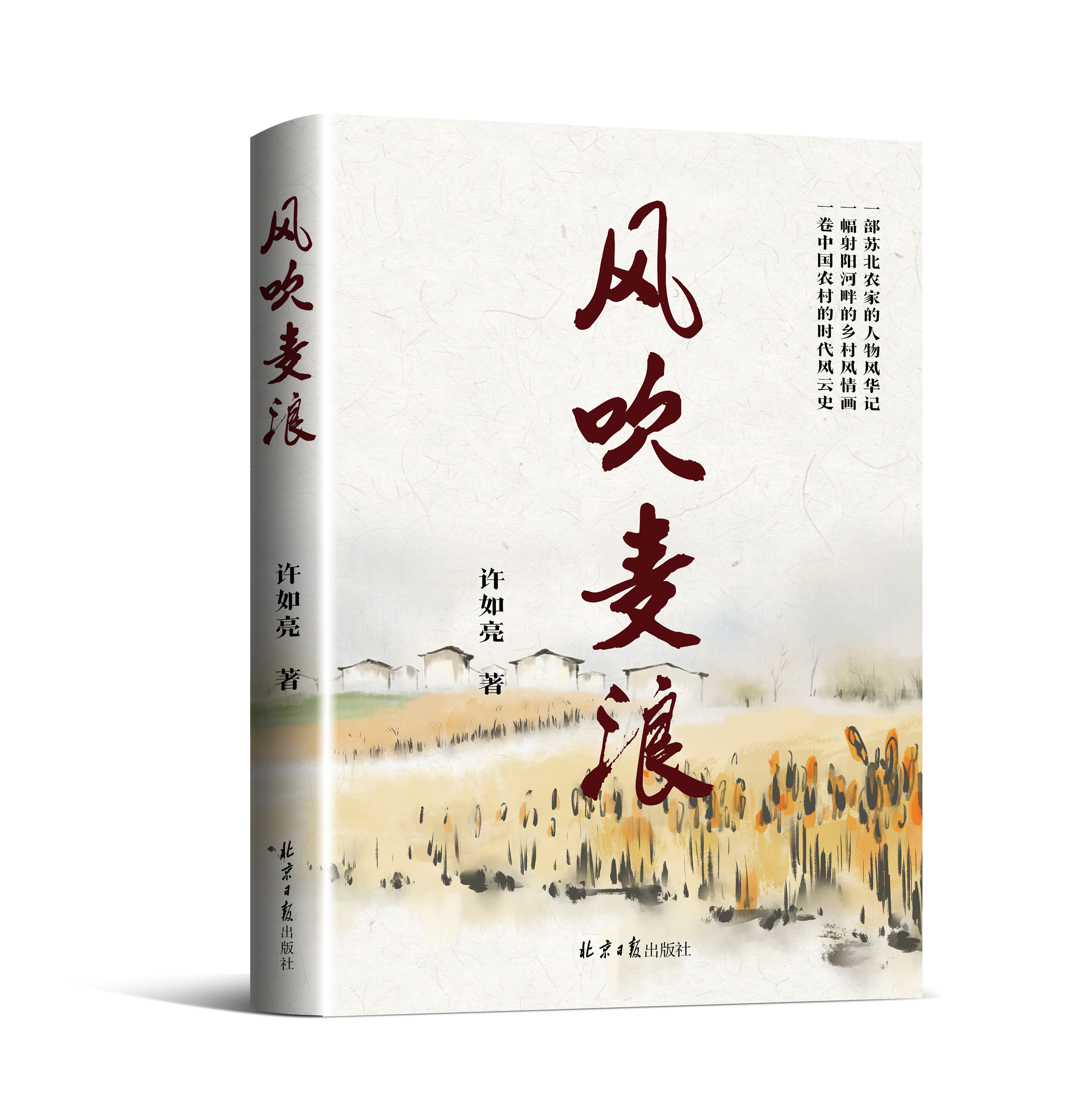
风吹麦浪舞 群像如画谱
——许如亮长篇小说《风吹麦浪》评析
高银
江苏作家许如亮先生的长篇乡土小说《风吹麦浪》近日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6章、28万字。书籍的出版不仅是一件文学盛事,更是作家文学理念的一次新飞跃,值得祝贺与掌声。收到许先生亲笔签名赠书《风吹麦浪》,内心肃然起敬,用心拜读,细细品味,果然是大家手笔,于细微处见功力,在细节上显匠心,经典之作!
社会学家费孝通有一句至理名言:“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乡土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是延绵了几十年乡土文学的血脉。农业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自然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70后的许如亮生活在风传情,水含笑;海风吹,芦花飞;蟹砌楼,鱼虾跳的黄海之滨射阳河畔。他曾经从事基层新闻报道14年,并做过多年村党支部书记和镇科级干部,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他扎根农村、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是农民最亲密的伙伴;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是农民兄弟生活、情感、信念和生命认知的见证者、思考者;工作之余,用心用情打捞农村故事,用笔记录农村生活,解读农村生活,先后出版《乡村彩虹》《花儿满枝红》《许如亮文学作品集》等著作。
小说《风吹麦浪》以江苏盐城射阳河两岸芦苇荡、避风岗、槐树屯三村和水塘乡为创作蓝本,聚焦农民的生活、命运、情感、精神世界,深刻的展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未三十年间,盐阜大地上常氏家族九兄妹在大集体时代、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人生命运的演变,同时穿插进周边村落的人事纠结,诸如分家业、开荒地、包田地、收公粮、挑河工、争界址、抗灾害、搞副业等民众日常生活图景。全书是一幅射阳河畔的乡村风景画,是一部苏北农家的人物风华记;是一卷中国农村的时代风云史;更是一曲献给传统农民和乡土中国的深情赞歌。拜读《风吹麦浪》,感慨万千,有许多话要说,但思之再三,重点谈小说的三个精妙之处。
一、带着泥土味的人物群像
人物,在小说体裁类的文学作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影响着故事的进程和结局,还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如果把一部作品比作一座大房子,那么人物就是这座房子的梁柱和骨架。在很多著名的文学作品中,人们多是通过认识了小说中的人物才记住了作品。
《风吹麦浪》最动人之处在于对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每个人物都描写得生动丰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人印象深刻。老实巴交的常青树,是扎根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农民,是典型的“只管生不管养”的旧式农民形象,缺乏长远规划,面对困境愁眉苦脸却无力改变,他的“老实” 不是懦弱,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生存智慧;妻子伍月红则展现出惊人的生育“能力”和坚韧的忍耐力,“生娃不找接生婆、干活到临产”。不屈不挠的儿子常有理,是改革初期的“破壁者”,作为生产队长,他带领村民在改革浪潮中勇闯市场,用智慧和勇气改变命运。积极向上的孙子常笑天,则象征着新一代农民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他将现代技术于乡土情怀相结合,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常青树正直善良明礼诚爱情九个子女:友正(憨厚勤劳,与喜兰自由恋爱)、友直(残疾)、友善(早夭)、友良(有文化,省报记者)、友明(英俊,被迫联姻)、友礼(生产队长)、友诚(部队军官)、友爱(长女,打工者)、友情(次女,大学生),这些人同其他人物构成了苏北乡村的 “小人物群像”。
二、乡土化的精神图谱
射阳河的浪涛与盐碱地的风沙构成了农民生存的自然困境,而疾病、贫困、生存环境、政策变动则是社会状态的无常考验。小说主人公在这些困境中展现出的韧性,恰似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明知巨石终将滚落,却依然一次次将其推上山顶。伍月红因过度劳累病逝,常有理在改革浪潮中遭遇挫折,他们没有被击垮,而是将苦难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始终拥抱时代,砥砺前行。小说反映的不仅是生产方式转变的现实,更是这种现实投射出的精神进化,是时代变革中人的进步与生命的升华。“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农民们在盐碱地里种出高产小麦,在射阳河中捕捞希望,在“丁头舍子”里编织未来。他们在土地上的劳作与创造,正是他们造化精神的具象化。常氏家族是跨时代农民的典型,三代人的命运轨迹,折射出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韧性光大。这种韧性不仅是对自然困境一以贯之的抗争,更是对生命意义更高层次的追问。主人公在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站起,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韧性、尊严和拓展。常家人以血缘为纽带,在“己”的中心向外推衍,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网络既是束缚,也是支撑。当常笑天回村担任支书,他既要面对村民的传统观念,又要推行现代改革。他用“慢火炖,温水泡”的方式化解矛盾,既保留了乡土社会的温情,又注入了现代治理的理性。这种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平衡,正是中国农民生命韧性的全新延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未三十年间,是一个值得浓墨重彩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在繁衍生息的这片热土上,经历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变革,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转型,大发展。社会结构、政治元素在不停地发生着裂变、演化,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许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如何把这些异彩纷呈、充满活力、呼应时代变局的激荡流程呈现出来,如何在岁月长河里刻下壮美的印记,以及把文学坚定温暖的力量传递给更多需要认知的人?特别是根植于当代现实,记录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记录农民热诚、深切、努力的追求和奋斗,对于他们的梦想和追求,他们的苦难和欢乐,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他们的抗争和呐喊,以及他们对自身的肯定与否定,否定与肯定?这些完全值得每一位作家以心和笔去认真地亲近和审视,用笔记录下来,用文章展示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闪耀于人类文化高地的文学之光、理想之光和希望之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作者的乡土小说应运而生,脱颖而出,用乡土化的精神图谱提醒我们,文学不仅要记录时代,更要传递精神力量,鼓舞人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三、地域化的文学表达
支撑起厚重思想内容的,是极具辨识度、地域化的乡土语言美学。许如亮的文字仿佛浸染过泥土芬芳的种子,散发着浓郁的地方色彩。他对射阳河畔风物的描摹堪称典范:捕鱼场景中晃动的船影与粼粼波光共舞,秋收时节波浪起伏的稻浪与湛蓝天空相映成趣,清澈河水倒映着形态万千的云……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文字并非单纯的风景速写,而是将地域景观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
作者善用方言俗语却不显粗粝,比喻新颖贴切而不落窠臼。比如方言“赶头碗饭”“丁头舍子”“打请工”“四大碗/六大碗/八大碗”“山芋茶”“老霸王”“超支户”“二杆子”等,以及歇后语,如驴子下了个小兔子——一代不如一代,罐里逮王八——十拿九稳,兔子尾巴——长不了,老虎头上站老鼠——找死,机关枪打鸭子——呱呱叫,这些充满口语化、沾着泥土味的语言,使小说平淡的乡土气息更加浓烈了起来,使人读后乡音绕耳,油然而生悠悠乡情。
《风吹麦浪》不仅是一部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小说,更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探讨人性、催人奋进的佳作。小说的架构稳健,建材充裕,形体丰满,意境悠长;叙事质感而灵动,写人从容而真实;感情丰沛,意境美好;字间有天地,行里有乾坤;读来很耐、很隽、很生活;再现了生活,来于生活,大于生活,高于生活,远于生活,读来让人爱不释手。
会杜撰的人写小说,善抽象的人写诗歌,懂得生活的人来写散文;许如亮以笔为犁,以丰富的阅历,沾满泥土的的笔触,记录家乡的时代变迁和人事沉浮,深耕文学创作,这种对土地的热爱、对文学的执着,正是当代作家应有的精神品质。
最后,用掌声对许如亮以祝贺,祝:艺无止境,天道酬勤,文学天空越走越阔。
作者简介:艺术身份: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