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偕早期诗论二章
顾偕二十岁早期诗论二章
作者:顾偕
一、形象思维
别林斯基说:诗歌寓于形象思维。
究竟怎样才算得上是形象思维,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专靠众说纷纭是悟不出真谛的。这得根据作者的实际感受而作定论。
作者首先应注意:绝不能对抑制在自然界的事物的情感、外形,用一种写实手法,去客观地记录和描绘它们的本身。
其次作者还得时时抓住诗的特征,那便是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绝不是我们的日常思维。《文心雕龙》中早有“诗忌俗”的警策。
故此,现代新诗,就像西方的现代派画一样,往往是不规矩的。它既要排除“俗”字,又要化事物形象,在一种严谨思考下,以一种抽象的语言或超现实的笔触——点缀那些已经过思维夸饰或形象虚构后,渐渐从普遍性观念中分解出的实体。
许多读者常有这样的感觉:有些诗单就表面而言虽不乏“时髦”的形象思维,但细细一瞧,就发现这种“思维”有的竟抽去了逻辑的必然性。为此,他们对这类新诗抱有的偏窄之叹,时常啧有烦言。
事实并不都这样。一首真正寓于美的形象的诗,从来都不会超越逻辑范畴的。表象的气韵,往往更是循序着内在逻辑而急遽变化的。我们不妨拿这样一首小诗《雨》作验证:
你从云缝中挤了下来
孕着多少清澈的珠儿
缥缈降生到大地
扭着轻盈散漫的姿态
这首诗中的“挤”“孕”“扭”三字的词性是动词,古人谓之“诗眼“。这种诗眼在属于它的句子或整个一首诗中,起着深化和烘托形象的作用,自然也是诗中不可抽去的神髓。“挤”字成了“云下来”的枢纽,“孕”字成了“清澈珠儿”的窥测,而“扭”字则变为了《雨》的“散漫姿态”的情趣,如此水乳交融、五音喧响、则七彩纷呈。倘若这《雨》失却了上述三个诗眼,或用其他三字替代诗中的动词“挤”、“孕”、“扭”,就有眼无珠,无疑顿然失色。
司图空的《诗品》,爱好诗的作者想必是读过的。这书中的“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按现代语来译大意就是:(自然界的万物)——它们聚散流动虽有万数,收入笔端的只需想象中的一粒。
《雨》这首小诗实可谓形象思维的范例一粒矣。
新诗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同于其他文学,就是因为它敢将充满概念的事物,通过理性的帮助后,打破那种事物本身所存在的纯然规律:
她们萦怀人类的恋心
因此给大众挥闪了自己的春情
她们深爱地球上的文明
所以给这世界
撒下这多光洁的水晶
——顾偕:《星星的春情》
作者在一种主观认识兴趣的诱导下,毫无顾忌地让理性中的事物,化为了五彩缤纷的形象。进而放弃外形,捕捉神似,使之形象生机勃勃。
虽然形象大凡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材料,但经过诗人用新鲜思维和充满爱的虔心处理后,它倏然就形成了一团想要喷燃炽热情绪的欲火。这欲火,是形象的化身;这化身,是情绪赋予的;这情绪,也就是形象的诗了。这种情绪最初有时虽会在迷乱中“瞎窜瞎奔”,但随着瞎窜瞎奔的情绪,并不完全也在瞎窜瞎奔的形象的理智,此刻却牢牢揪住了诗人的神经。
莎士比亚说诗人是充满想象的“疯子”,这定论,应该绝不是带有普遍性的那种。纵然诗人感情确实是够疯的了,但形象赋予诗人的思想,往往却是清醒而明智的。形象思维并非意味着可以胡说八道。
亦即:诗歌——形象思维——不是呓语。
所以我们认为:美的诗,真正的诗,不仅要有形象新颖的表象、意象,还要有思想厚实得单纯的内核——尤其在新诗中,形象和思想,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哪怕在旧体诗中,亦不妨如是观。
古代舞文弄墨的老夫子,往往会惊叹“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杜甫)之类的华章佳句,甚至会忍不住拍案称绝捻须晃首道:诗惊鬼神诗惊鬼神!然则何以惊乎?便是诗中常有暗暗盘旋着的思想与形象的星火!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象于笔端”(陆机:《文赋》)。诗的形象思维,以此广发胸臆,美句自是则当流于唇齿。
二、朦胧诗
近两三年诗的阵营出现的“朦胧诗”与“明朗诗“之争,看来还末揠旗息鼓。
我们想单就这个问题继续絮叨絮叨。
新诗蜂拥,风韵各异。诗言志,有感而发,无感而休。明朗诗是诗,朦胧诗也是诗。有诗,是诗,就应该写;是情有爱,便更应当抒。文学创作容不得优柔寡断。
歌德说“现实应该有表现的权力。(《哥徳谈话录》)
问题在于,当今许多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诗。很多青年(包括写这种诗的作者)甚至并不了解真正朦胧诗,究竟为何物。没看清裏着“朦胧诗”帷幔的艺术,就恍恍然兴味织起“朦胧”的图案来。他们以为能扯来一件“诗的罗裳”,拣来几个诗的韵脚,然后给句子分行的“整体”穿上,眼前呈现的,就是自己愈看愈满意的诗之“新娘”了!
孰不知,真正的诗,真正的朦胧诗,单凭他们这种愚顽的匠心是不能斧凿而成的。然而有些编辑部的大门,却很是欢迎这种“新娘”的光临。
然而这种“东施”般的货色,又怎能让见过“西施”的人觉得——“效颦”者的美呢?
然而类似这种冒着“朦胧诗”牌子的句子,仍还源源不竭地萦绕在读者迷糊的眼帘!
究其因,有些编辑也并非完全理会这样的“诗”,或认为这样的诗就真是诗。但擎着“朦胧”牌牌的或因是熟人是名流是常客,更或是诗坛众所周知的新秀。可能这类“诗”正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故此灵巧的编辑为处理这样的诗,一来不想驳了“名流”之类的情面,二来也不忍心将到手的时髦作品委弃——发它篇把两首又何妨刊物的质量,即使自己弄不懂,不是还有读者嘛,大家都来圆下这个“朦胧的梦”,不正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上粗略涉及的,大抵是读者对朦胧句子多有排斥的事由。
露,永远不会融为感情的眼泪,正像冰,也永远不会凝结成粲然的水晶。让我们一起品尝一首真正的朦胧诗吧:
从你,我看到了那在大海处
渐渐宏伟地扩大并展开的河口。
——惠特曼:《给老人》
这是首用一句话构成的诗。
它句子虽长,但结构严谨;立意含蓄,形象精简。在一般不能立时明瞭诗人独具匠心的读者眼里,这样的“给老人”,委实够朦胧的了。
诗人在先对具体现实——“老人”这一形象变形认识后,立即再由“从你”的概念里,去抽象地联想到大海的功能,进而通过艺术渲泄,把对老人的理性与一种高于老人的事物,维妙维肖地联结在一起了……
这种题显义隐的写法,不仅为读者摄下了能够久久揣摩的镜头,还在读者思路前,展示出了一种深邃的意境。就诗人本身而言,这种写法既能了却他《给老人》寄寓丰厚形象的心愿,也可以使他从经常委身带有普遍性的形象中,将一种压抑的事物,通过思想深刻的改造,用情感就此释放发抒出来。
所以诗不是广告。那或有美的形象,也不能美得如雕镌的裸体,直接明朗,势必会丧失诗的个性含蓄。何况我们在这里谈的还是朦胧诗。
因此真正的朦胧诗,应当只属于类似《给老人》这样的作品,当然这样的范例自是枚不胜举。
所谓读者看不懂的朦胧诗,其实那都是些冒着“朦胧诗”牌子的——朦胧诗的赝品。当思想和感情得到痛快的表现时,谁能不为智慧的光临而感到欣喜?尤其这种智慧已创造了一个倾注了感情和思想的艺术生命时,谁还会老去不遂地品评这生命相貌的“朦胧”或“明朗”?
所以我们认为:真正的诗,自然或偶然地都综合着美的分子;真正的艺术,无论明朗还是朦胧,均将首先融入美的生气。
为什么总有人爱把正在“雾”中峥嵘的妙景,看作是再也露不出真面目的“朦胧”幻相呢,不得而知。
为什么总有人想把由灵感艰辛铸就的一种带有创造性整体,莽撞武断地用陈腐观念将其抹杀呢,不得而知!
朦胧诗就让它朦胧诗嘛,何必这么多流言蜚语。
“诗有恒载,思无定位,随性适份,鲜能通圆。”(刘勰:《文心雕龙》)一个作者,根据自身特点,只能在他所属“特点”的范畴内,较大值作出有成绩的事业;只能在他对这种“特点”不歇地发挥和修正后,有所更大的突破。关键是,朦胧诗的“通圆”者,近两三年诗的阵营,能有几人欤!
由此,我们为这样的诗人能视境于心、驰思于情,在“适份”朦胧的艺术中,能够渲泄了真实而美的朦胧物境、情境、和意境,真诚地欢呼和祷祝。
1981年10月15日于湘潭黄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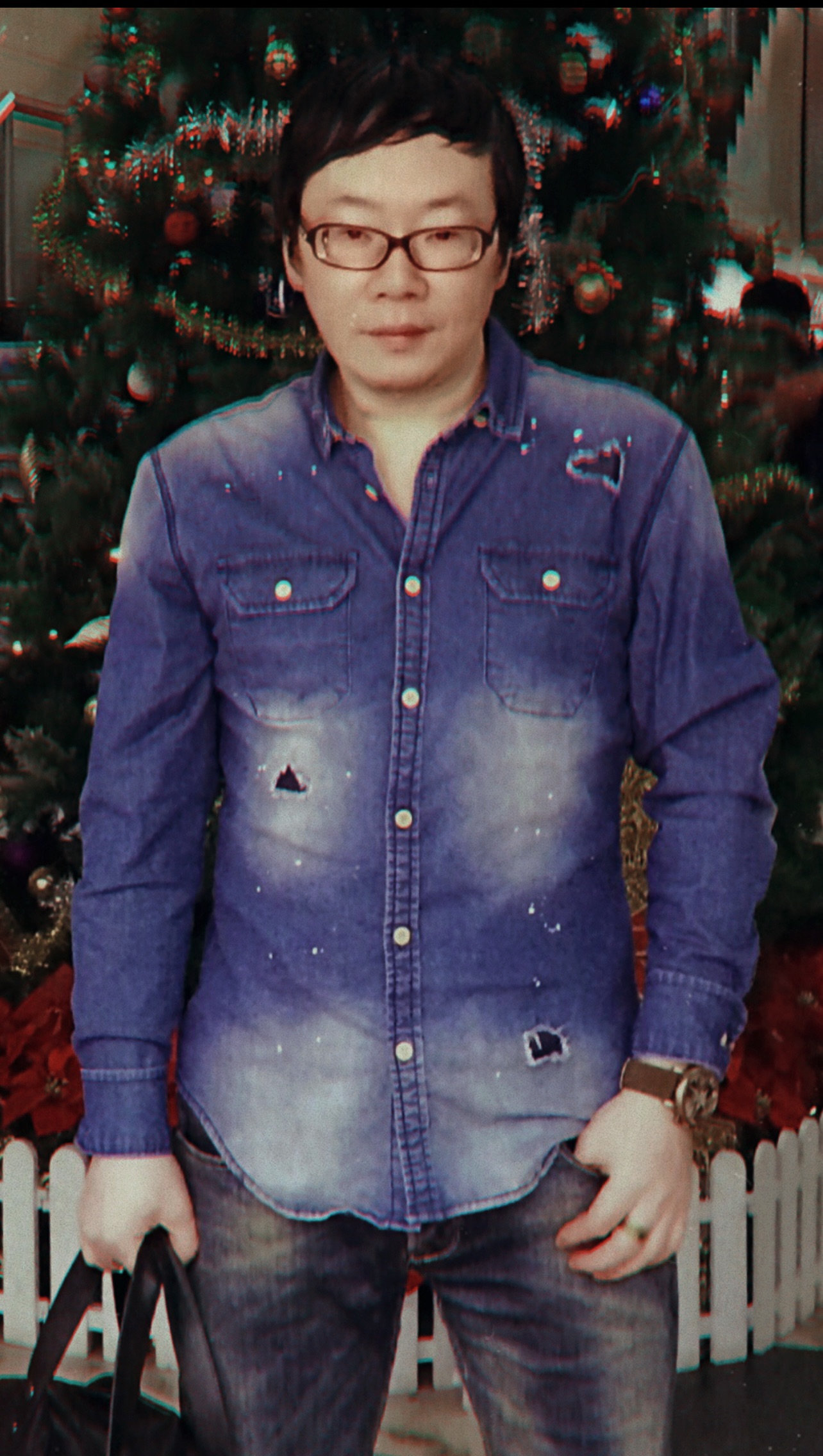
顾偕 中国作协会员、广州市作协原副主席、当代著名诗人和思想批评家。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