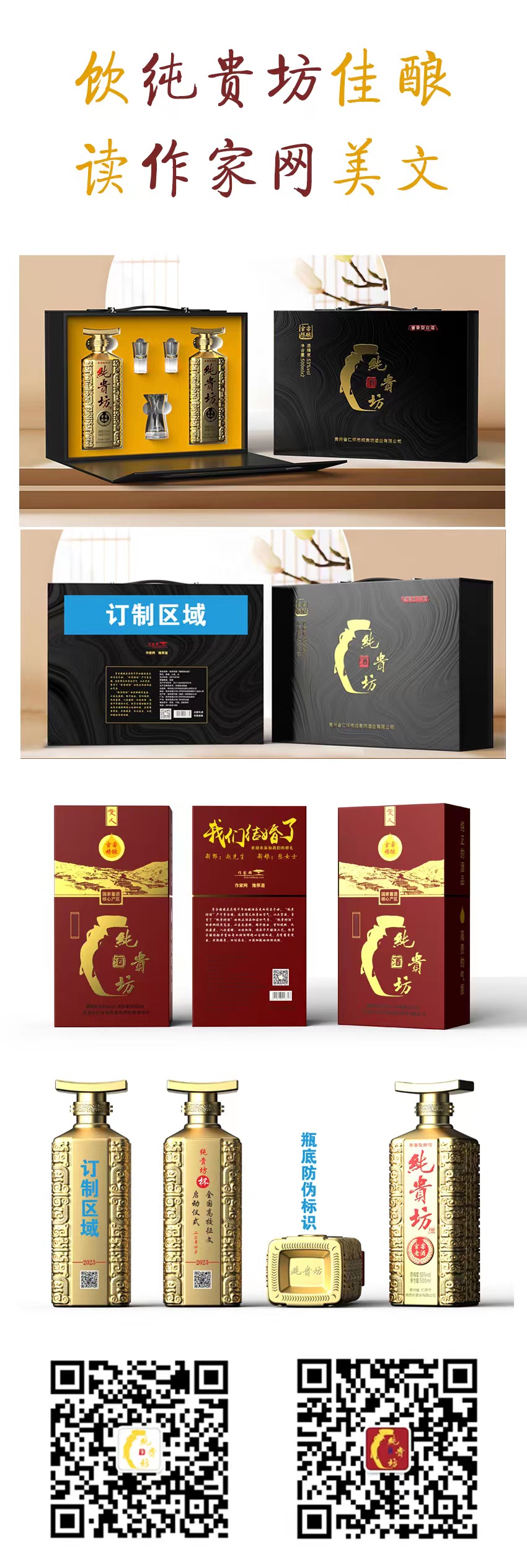诗和哲学彼此相像
诗和哲学彼此相像
——赵野《渔樵》评解
作者:陈亚平
我觉得,赵野诗歌最大的可读吸引力,绝不停留在雅各布森式的把语言唤醒,也不是为了讨巧当代,来借鉴他向往的古代。他的秘密,是他对语法改变的规则。我觉得,语言唯有被心智表达,才能表达出心智。这一点,赵野做到了在过去的现在中,找到现在的未来。因为过去,绝不是最终的,在超无穷可分的最终之中,还可以运化出新的。这放在当今国内诗界,绝对有一种人人可知,但十分不好做的独有性。赵野从语体的骨子里契合这种命中注定的独有性。这让我想起博尔赫斯颖脱于卡夫卡的奇幻小说,不过,转折性决定博尔赫斯这类小说成败的,取决于博尔赫斯在诗性上对奇幻叙述的重构,而不取决于对卡夫卡奇幻叙述的模仿。博尔赫斯小说那种垄断感的超常规理解的伟大,在于他能用前哲的奥义,激活他自明的奇思,再通过诗式的意识流、诗剧的跳跃性与非三一律结构的故事流,偶合在一起,形成颖脱于卡夫卡。
我解释力的点是:在“偶合”这个话题上,赵野也钟爱写一种借诗阐哲、以诗寓禅二者偶合在一起的诗。但赵野这种言志和阐导二者跨越的边缘体,在变通传统的范型上,既要从白话中选词,又要炼意,所以说难之又难。弄不好,会伤到双方中任何一个单方。这种巧合背后的严苛和灵犀,很难得有人碰。从诗歌句法的功能看,赵野嗜好的方法,与其说是唤醒语言,不如说是提出了语言的协同原则。比如,开放语言的相互张力和兼容性,来追求混合语体的协同。
赵野新作《渔樵》,我感觉是对他长诗《碧岩录》精气和神理的一种蝶变。《渔樵》更体现了赵野与禅理、易理、诗理之间,越来越接近自我登顶的大化弘境,更留心一种玄览中渐悟或顿悟出来的,更宏深的文化宇宙……。禅机和易理主题,尽管在国内朦胧诗前后时代有过,但仅仅算是语言用法潮流中的一个支系。
延伸地看,《渔樵》诗境的成体、发展、转折、完成,只是顺应着赵野思想中生成的跳跃力,来体现情节组织的长度,读起来,有破解古代哲学谜底尽头的那种深邃。这类诗,让人觉得是中国式玄言的毕达哥拉斯体——这种仅仅是赵野的楷模文体:短句的断片,在断崖中崛起异峰,在连缀中又凭空断裂,这体现了思想转智成诗、转诗成识的一心开二门的妙性。
从诗性的功能看,赵野《渔樵》和杨炼的《易经》有根本的不同。赵野看重,诗有音流和制约词、句组合方式的那种既好听又好看的视知觉,在延绵中去掉运动,在涌现中持有隐匿。所以读《渔樵》中的“周易”,会从诗性的存在,而不是感怀某个存在者的神秘,来理解诗境和易境的互助。
我引一段杨炼的诗作《易经,你及其他》:
“六十四卦卦卦都是一轮夕阳
你来了,你说:这部书我读了千年
千年的未卜之辞
早已磨断成片片竹简,那黑鸦
俯瞰世界万变而始终如一
……
给所有读这部书的嘴打满补丁
月亮和大海同样盲目,陨落或升起
浸透谎言,像一条自如的鱼
深渊忽略着时间,你从皮肤开始
伤口用尸布缠了再缠
当猝然发现,心也是一只黑鸦
你,你的等待,又已千年 ”
我再看赵野写的《渔樵》诗句:
“九四,或跃在渊,清风与明月
站在我这一边,隐喻发出新芽
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
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
诗中“九四,或跃在渊”是《周易乾卦》卦辞原文。汉代哲学家王弼在《周易注》中解读为:“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解读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跃,羊灼反。或者,疑而未定之辞。跃者,无所缘而绝于地,特未飞尔。渊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测之所。龙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跃而起,则向乎天矣。九阳四阴,居上之下,改革之际,进退未定之时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随时进退,则无咎也。”。
比较王弼和朱熹的卦意解读,会发现,《渔樵》诗中“九四,或跃在渊”与诗句“清风与明月”形成了一种前后句子,互相参照但没有互相指涉的互文效果,“清风与明月”诗句是对“或跃在渊”的文本创造和文本补充做出的一个铺垫,接下来,诗句“站在我这一边/隐喻发出新芽”的意义构境,依我看,就完全是变向的、位移的、为对应自我意识而经过刻意开创的。它以一种深入到卦意内部的若断若续的隐形对话性,把《周易》“或跃在渊”透现出的意蕴点、诗质点、想象点,做出了先吸收,然后再无而忽起的重新化生。
我觉得,重新化生,在于先有的诸行相生,化生的开创总要先于化成的可观。读解“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我会发现,诗句的字形、句形,本源上是现实场景和图景的外现,这些好看的句形,所集合的字形,就是妙观的天地人文图景。而字形的发源和演化的过程性,本身就统一在自然的总体发展过程性之中。字形,既属于自然物象美的分形部分,又属于心灵对象物的分形部分,具有着存在者的本质。诗句字形整合的视觉表征,就是一种能呈现心理声象和心象的原初认知,它对心境的刺激是有极大促变作用的。它不仅会使人联想到字形,对物象的图景还原和场景的想象式改造,还会让视觉构形的感知,转换成一种诗意的愉悦美感对心境的激活度。
诗句“隐喻发出新芽”,依我看:表面上,诗歌和隐喻的关系是诗的方式的独一化。但事实上,隐喻与哲学之间,也有无蔽的关系。无论诗歌还是哲学,本质上都是要由一种感性的本义,来实现另一个更广泛智性的转义,换句话说,由身体感官的图式,向心灵感官的理式转渡。从这点看,有机的、有机械背景的隐喻范式,是用人类话语导图的前示性,构成了一个唯隐喻化的思想宇宙。隐喻也因此成了,人类思维途径中永远无法绕过的、神一样的先决者。比如,用小说来写哲学的诗人博尔赫斯,他从不拒绝但又非常在乎的是,只有隐喻那种新的变化,才能超过既定的几个主要模式。”他的说法是有哲学根据的。我觉得,如果隐喻长期固定的、循环地去重复几个模式,就必然要限制一种隐喻的未完成性。隐喻的未完成性,正是思想的重构处。
赵野说“隐喻发出新芽”,这句“发出”,就是赵野对隐喻固定主义的一种解构。诗句“站在我这一边”,不仅仅是指赵野理解隐喻的方法立场,我深一层的评解是:也许换一个直觉,换一个联想的源头,换一个体验的目标,或者,再换一个想象搜索的未知点,那么,隐喻中那些曾用光了的感性,有可能就会重新积再蓄强力。但不可回避的是,既然能够“发出新芽”的隐喻,成了人类思维途径永远无法绕过的、神一样的先决者,而让人类别无选择。那别无选择本身,就意味着一个可无代替的极点。那这个极点,会不会有它可能的反面?
“隐喻发出新芽”,这句诗,反映了赵野近几年对诗的思想化命题的先驱性思辨之一,与哲学上的重构性差不多接近。我觉得,重构的隐喻,在潜能中,首先应该存在一种开放其他表义空间的大几率,比如,起码应该向一种有真理性的表义空间重构。因为从身体感官发展到心灵感官的隐喻性,它用类比想象和联想的物感直观,所引申出的,总是与超验普遍的东西有关,而且总是处在连续变化过程中的。大家都知道,人生如梦。这个比喻就有真理性的表义空间。人生本来就是,在梦一样幻即幻离的现实中,延续着实现了的幻现。
从这个意义上,诗句“隐喻发出新芽”,能够从“或跃在渊”的卦意渊源中,奔突性地跳跃到对“隐喻”的运思,这对《渔樵》的语篇格致,是有原创性拓宽力的,有感应而改构的。所以,赵野写出“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这个比喻新颖不新颖呢?光看这一句还不能肯定,但连着读完“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这句,就会觉得,它激发出了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东西的诡异结合感,而且还深深地划出一种真理性表义空间的奇特的限。因为诗句“邀星辰、真理和亡灵进来休憩”,就是邀请《易》、语言、时间——这些存在者,进入存在的“一座房子”。诗句把诗歌,隐喻成一个“搭盖”存在之家,这形成了一种真理性的表义,它对隐喻的重构性,是哲学上的。我认为,诗歌——这种存在者,不是预成的,更不是现成定性的,而是生成的,运化中的,是开放的未定型的一种存在者。但它只是存在外现出来的一种可感经验的存在者或外显者,而不能代替存在。本身存在,就像“搭盖”一样,能把存在者存在出来或生成出来。
“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采用了感性表象创造出的起源性质的想象,它有非原初性、非类比性、非现时性的特征,而且由感性,向非感性的形上世界做出了一种原创性的转移。另外,赵野通过运用新的联想,来组合诗性词语和非诗性词语的织体“搭盖”,这个“搭盖”的词准(一般人可能只用“搭建”),体现出他对潜在的“是”与“易”,产生了一种从内在可能性中掌握的运思。“我写一首诗/像搭盖一座房子”虽然不如“人生如梦”的真理性通俗,但毕竟是达到了“发出新芽”的真理性。
我再来讨论《渔樵》另外的典型范例:
“初,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
内心的善恶确立,做一个好人
神的训诫被截断,魂魄与祖先
接通,一起游走在共同神识中
文明不能遗赠,每一代人必须
重新学习,找到一种新的使命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对历史的判断要存一份原谅心
九五,飞龙在天,被年岁报废
语言一旦落地,势必负起责任”
诗中“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表现了赵野对《易经》离卦第三十:“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化解而再赋予新意的一种艺术手法,特别是用“江河”、“地”二词化成出来的构境,在与卦辞“日月”的对应中,更展衍了一种玄远。““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依我看,就是讲“日月”与“江河”的有限物象实在,进入了无限物界“天”与“地”的过程。确定的“日月”、“江河”的过程,是有限的,也可以认为是有形的,而将要发生的新过程““天”与“地”是无限的,也可以认为是无形的。诗句同时也隐喻了,实现的过程是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而未实现的过程是可能性成为虚拟性或自由性。在过程的一种未完成性中,我可以领会这样的诗境:
“文明不能遗赠,每一代人必须
重新学习,找到一种新的使命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
对历史的判断要存一份原谅心”
这段诗分成了“每一代人必须重新学习”与“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交互的关联是未定的、互动的,本身就处在过程之过程的生成与不断创化中。从诗句预示的广义的文本关系来看,“每一代”文本,都不可以对前文本,只作代际上一种同质的模仿,而只能是,对更多潜文本的替代式思想改换,或在一种文体增扩的优化式净化中,脱离前文本限制,来“找到一种新的”接续。
“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从字面评解,就是对《易》预含的一种存在的过程性的了悟,这种对过程性存在的一种哲学玄思,也是自然、人类、诗歌、文化、思想宇宙自身不可解构的魔化结构。依我的过程哲学来讲:诗句“一切都在变”的意义指涉了,一种未定的过程都是可变的,都是一种不断向后的、向或然性的一种待完成性。所以,表现为可能存在着或或然存在着的潜无穷的开放性,同时也是存在的向内回复自己本身前过程的临起界。过程,是自己本身的对方的一种相互依存,而过程的对方就是它的否定的另一个新过程。
“上九,夕阳山外山,物岂可穷
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
“上九”一词,是赵野用《周易》的阳爻,来给《渔樵》的正诗作一个起句,接下来化用龚自珍“吟道夕阳山外山”,是对阳爻歌诗性的互文铺垫,最后再展衍出诗句“物岂可穷”。这句是赵野对《序卦传》曰:“物不可穷也”诗质不履旧迹的互文性改构。连续两个互文的运用,就克服了《渔樵》对《周易》卦意的平面类推和线性演绎。我觉得,这种改构的关联性,让《渔樵》的每个句子,不仅有互文性改构的几重对应语义,而且还有隐含了几重对《周易》卦意的补充性阐评意思。这就让《渔樵》的诗性构境与《周易》卦意的诗质,形成了同源异构性的一种互文效果,它与哲学含义上的解构性一样,突破了结构上的方法束缚。
诗句“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是对“物岂可穷”的异质性跨一步的阐评。这句阐评,是赵野从全知叙述的角度,来表现的,明显带有一种自我思性横空跨越的突转性和断崖性。这样,“变易一旦开启”诗性改构的文本落点,就不会封闭在《序卦传》原文卦意的渊源同质性上,而是与《序卦传》卦意之间,平抑中有深曲,奇逸中带奇崛。
“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诗句,让我认为:诗歌审美的本质,也在于,以有限之在与无限之在相交的过程性。从这个层面说,哲学的元基质与诗的元基质同构于“变易一旦开启/谁敢放言结局”的过程性——这一核心。可以说,诗的终极审美关怀,就对应于过程生成这一哲学的终极关怀。或者说,诗的本体,对应哲学本体于过程的终极之中,这就是诗与哲学内在的相像。
《渔樵》在长诗的写法上,发展出了三种恰如其分的创意体:诗评体、漫思体、诗论体。这三种体裁的衔接很武断,但结合得很适合启思体的那种长诗的超逸,同时又有很深阔的文化负载度。所以《渔樵》的诗评读起来像史论,史论读起来又像漫思录,漫思录读起来又像随笔诗论,但三者合在一起,又像带有一丝玄学性质的文化宇宙地图启思感。
按我读解,赵野《渔樵》的原创动力,首先在于,《渔樵》把《周易》断语的格致,化育成了赵野自我重构诗歌原型的一个激活点,而人为地,在《渔樵》中扩展出了一种现代诗与《周易》诗质话语产生临近性和互助性的文际空间。这种文际空间,客观上,形成了有对话关系的互文艺术性,让《周易》的言说主体,对应着《渔樵》的言说主体,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的张力。其次,《渔樵》各个诗段单元之间的衔接,按《周易》卦象的可变性,来建立一种互动的呼应性,使得《渔樵》篇句的结构,有了不可用逻辑推导的随意跳跃性。再次,《渔樵》不重复《周易》中的同一思想,而是全力在自辟的理境蹊径中,不与《周易》的卦意渊源,产生一种重合。最后,《渔樵》偶有分解《周易》卦辞片段的原义,来对《渔樵》预设的诗境空间,做出一种另辟蹊径的奔突性展衍。这四点,就构成了赵野《渔樵》的改构性动力。这种改构性特征,在他的划代性长诗《碧岩录》中略现雏形。
2023年4月2——6日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