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发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答谢辞
陈先发2017-04-28 12:53:08
陈先发:所有成熟的写作都跟一种自觉的困境意识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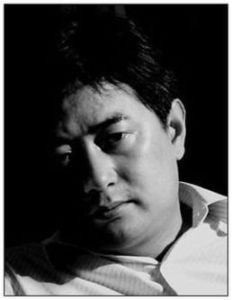
陈先发(资料图)
谢谢主办方和评委会。谢谢在座的诸位。在我们这个荣誉的授予与接受已变得相当轻率的时代,在此获得一个以取向庄重、过程谨严而赢得普遍尊重的奖项,我感到非常荣幸。
今年正逢新诗百年,这为今天这一刻增添了独特意味。百年来中国社会遭遇的巨大动荡与灾难、巨大撕裂与变革,不仅史所罕见,更是深刻投射到了个体生存和各类型的语言实践上,并将更长远地溶进我们各自的墨水中。无论秉持什么样的审美与创造取向,这种投射,都已或显或隐地成为写作中不能回避的强大干预因素。从百年这一时间节点回溯,经过曲折与深省,新诗生态终于成为一个审美维度日趋多元、内在层次更为丰富的独立存在,既独立于古汉诗传统的典范语言经典,也日渐独立于我们曾置身其阴影中的西方现代派语言经验。当代汉诗在对个体尊严与生命意志的赞美的轨道上,以更具活力的语言方式探索着人内在的冲突,在语言中呈现人之内心光影交织的本真状态。这个成就是了不起的。不过让我稍感遗憾的是,至少我的视野中,迄今尚未产生足以匹配这个时代复杂性的伟大诗人与典范作品。
在我看来,所有成熟的写作都跟一种自觉的困境意识相关。以诗之眼,看见并说出,让日常生存所覆盖的种种困境在语言运动中显现出来,让一代人深切地感受到其精神层面的饥饿——正是真正的写作所应该承担的。前一段日子,我回到老家桐城乡下祭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到了人口加速流失的村庄的凋敝,老屋倾塌,荒草高过人头,昔日内质温润、鬼神俱在的多空间的乡村,正在衰败和死亡。同时,千镇一面、个性荡然无存的新镇建设将劣质城市化运动演绎得如火如荼。财富迅速增加的乡村表情中,赤裸的攫取欲与永难自足的焦灼感毕露无遗。这种对抗性景象几乎让原本被遮蔽的时代困境完整地浮上水面:一种物质与信息过度累积后的匮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时地地,这种匮乏像影子一样强烈地附着在我们身上。对诗歌而言,这种匮乏既是某种枯竭,也是一种源泉。时代把这样的资源,馈送给今天的诗人。我在《菠菜帖》一诗中有句:“我对匮乏的渴求甚于被填饱的渴求”。我看到匮乏,匮乏就是我语言探索的桌面。假如我看到的是平庸,那么平庸作为一种资源被揭破与榨取,它所蕴藏的能量同样惊人。
这就是诗性的力量。当你看到的桦树,是体内存放着绞刑架的桦树,你看到的池塘,是鬼神和尺度俱在的池塘,一切都变了。语言在此会爆发出新的饥渴。诗是对“已知”、“已有”的消解和覆盖。诗将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语言中变成“未完成的”,以腾出新空间建成诗人的容身之所,这就是诗性的“在场”。正如量子纠缠等新的科学实践一样,困境意识作为一种写作力量,推动我们在语言实践中不断为世界构建出新的神秘性,使神秘性本身成为唯一无法被语言解构的东西,并因之而永踞艺术不竭的源头。
诗学就是心学。无论科技或现实之力如何突破想象的边界,一颗感通天地而游于万物的心是无可复制的。心性与性灵,不仅是语言的源起,也会是语言创造的最美果实,更是人以其卑微来对抗虚无的最后手段。所以,成为更内在的人,仍然是诗学上永不会终结的理想。愿我们都在此实现心灵的自由。谢谢大家。
文本为陈先发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答谢辞。
授奖辞
陈先发的作诗之道,重修辞,亦重哲思。日常生活的艺趣,暗藏生命的忧思;古典意象的重写,映照现代的魂魄。俭省的用词中,不乏细腻和心裁;沉静的情感里,也有悲怆和痛惜。他出版于二〇一六年度的诗集《裂隙与巨眼》,诗风繁复、多义,心向传统时,终古虽远,读之如在眼前,而更多的时候,他则以先锋意识来锻造语言和提纯精神,新意昭然。这种新旧杂糅、古今并置、温和中透着锐利、怅惘中渴望超越的诗艺,在当代诗界并不多见。
作者:陈先发
来源:中国诗歌网
http://www.zgshige.com/c/2017-04-25/31747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