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港的船
北港的船(短篇小说)
作者:段文昕
1
汤从锅中溢出,小怡急跑去关火,泡沫如潮撒了一地,她不由得讨厌起林昊的不请自来。
台风前夕是村委会最忙的时候,作为文员,小怡要通知渔民把船停到避风港,叫独居的老人来服务中心避雨。周伯伯、赵阿姨,她正按名单一个个拨过去电话,却意外收到林昊的消息。
“你在家吗?”他问。
小怡没回复,这半年他们的交流全是空白。像是等不及,林昊又打来电话,说自己正在对岸海岛调研,就隔一座铁桥,能不能来找她。小怡看向窗外,气旋临近,云层正为雨水蓄力。小怡的沉默就是应许,她想林昊会知道的。
从村委会回家,她急着将地面拖干净,解开袋子,蒸鱼,仓皇地把姜碎洒于表面,青菜的水没沥干,滴滴答答黏在身上。小怡才发现自己在气恼、紧张,不为长久未操持的两人晚餐,而为意外将有的会面。
父亲的死就像电流,打乱了她和母亲的意志,半年前她辞职离开上海,留给林昊的解释很少,尽管他说可以两人一起承担。小怡记得那天母亲发来的语音,颠倒混乱,又字字清晰:
司机,该死。杀人犯,知道吗?撞到人还不承认,要往后倒。本来只是摔倒,从车上你爸爸跌落还磕到头。想爬起来,视频里面他站起来的,结果司机倒车,整个人都卷进去。老天爷。
父亲的车祸登上本地新闻,用来警戒多事的十字路口和不爱戴安全帽的车主。她反复看监控视频,进度条还不到半分钟,比刷过任何一则无聊视频都要短。父亲样貌,如同母亲用的形容词一般难以辨认,又精确遭受同等的痛。早晨父亲照旧骑车去上班,转过红绿灯,就到他最爱的海蛎饼店。
小怡决定回家,发完辞呈,她匆匆赶往下午的动车。小怡不常回福州,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上海实习,和林昊相恋,两人租的单间就算是家。只有春节,沾了喜气的假期,她才和母亲、嫂嫂一起吃几顿团圆饭。这次回去,一切都变了。快走到家门口,小怡才发现视线里冒出一栋蓝白色三层自建房。母亲在远处停下,挥手让她快跟上。
这是郑阿姨春天新落成的家,母亲感叹,你爸爸没福气,等不到这样的房子。
回到家,嫂嫂将小怡拉到一旁,反复说母亲疯了,“她真的疯了,居然还要我儿子给他穿寿衣,小孩才六岁,多遭罪啊。”小怡吃了一惊,她以为丧礼本该由自己操办,没想到母亲却坚持,要遵循祖宗留下的道理,一切留给男子,哥哥不在,就轮到哥哥的儿子,六岁的杰杰。
双腿盘坐在地上,小怡听见嫂嫂和母亲还在争吵。母亲拉出糨糊般长句,平日大概也是这样,但嫂嫂管钱,向来是不听的。直至听见笔筒砸地,她也烦了,起身要去制止。碰见嫂嫂摔门而出,一双眼被泪洗过,爬满毛细血管。
“这是你们家的事,我又不笨。”嫂嫂指着小怡的鼻尖。说完,两边都安静下来。
楼下停尸,痛到不能再痛,竟还剩一种加班的心情,小怡反复核对清单,在微信群里发追悼会时间,一遍遍回复亲友之节哀。林昊从哪得知的消息,她也不知道。第一顿晚餐,小怡听见母亲在厨房剁肉碎的声音,很用力,如同要把另一部分从家里剔除。做饭的权利也是母亲从嫂嫂处争来的,还有接送杰杰、在路上乘机劝服他,一并成就母亲最后的颜面。青蓝夜色里守灵,她第一次看见父亲破碎的样子,不忍别过头去,血迹板结,经碾压的五官,勾勒他的挣扎。她极力在心里找另一张脸,那是父亲带着她和哥哥去海边,赶在日落涨潮前。忽然盐雾翻腾,浪花和气泡都凝成透明液滴,浸湿了刘海,小怡额前有傍晚的温度。三人自岸上往底部爬,落脚之处,海蟑螂如声浪散开,密集的黑色虫体,留下一阵皮肤战栗。
小怡左脚的鞋掉了下去,父亲的脸,隔着石缝冲她笑笑:“你下来,有我接着你。”
父亲仍在微笑,风灌进裤腿,终于摸索到石底。父亲紧牵她的手,指一块斜出的棕黄色巨岩,往上看,天被切割成一线蓝,海映在身后。
是那样的笑脸,如今躺在小怡面前。
最终还是由堂哥带领,杰杰替父亲整理,净身,换寿衣,出殡。六岁的杰杰很配合,知道适时该有哭声,放肆的眼泪里,不知是否藏着真正的,属于孩子的悲伤。小怡步步紧跟,队伍在唢呐声中越拉越长,从家门口一路走至镇上。她的左手扎着一段黑色棉布,装有骨灰的棺材在眼里热变了形,分割成棕白两色。
那日太热,青烟叠加高温,灰黑色的人群里充斥着眼泪和浓重鼻音。客厅内新装的空调,很吃力地制造冷气,等上菜前,人们把水泥地踩得踢踏响,用本地话细数父亲的好日子。儿子出了国,女儿还念到大学。有出国的命,到底是一桩幸事,可惜还是福薄。女儿可要抓紧,早些结婚。
忽然,她接到林昊的电话,说自己在村里迷路了,绕来绕去只看见村口的牌坊。小怡一面溜出来找他,一面叮嘱,倘若碰见一栋三层高的小楼,蓝色屋顶和白色罗马柱,后面屋子便是。
回来时林昊已站在门口,站在黑白分明的讣文前。小怡只好带他进去,屋内极闷,余火未烬的热度,借来的两台电扇如守卫立在父亲像旁。该怎么向母亲介绍,小怡犹豫着,不免感到一阵轻微的肠绞痛。
“这是公司小组领导,平时很照顾我。”
小怡说完,母亲含着泪道谢。
“真遗憾,”林昊说着,“小怡失去父亲,我们也没能留住这么好的员工。”
林昊执意地来,又不挂念地走,跨过门槛,小怡没能多送几步。只留下烟混在香坛里,散出一股节制的哀愁。她想那该是两人感情的终点,虽没有向父亲解释,但他一定能看见。
隔日黄昏,小怡收到两箱自上海寄出的行李。像当年搬进林昊家,小怡又将东西拿出铺满地板。她惊讶于林昊这样爱搜集发票,打车、餐厅、咖啡店和面包房,消费的每顿双人套餐。林昊都整理好,丝丝缕缕还给她。
2
天地浮动,头顶有海雀成群游行。大家做着台风前的打点,晾晒在外的渔网往回拉,扑腾一股晚到的咸腥,扯下来的海草长满地。
郑阿姨敲响小怡的家门,问她借黄色胶布。
“家里本来还有,但新房子,装修过,怎么都找不到。”
听完,小怡苦笑着,将门轻轻拉开一条缝,留郑阿姨立在廊前。拿完胶布,郑阿姨却没有要走的意思,眼神掠过屋梁上的父亲遗像,嘴里嚼着房顶高真好,这么闷还有风。再问家里怎么就小怡一个人,难道和妈妈吵架了,女孩子自己住多不方便。
郑阿姨爱讲道理,小怡早就听惯了。郑阿姨的儿子和哥哥一般大,女儿也与自己同岁。自幼两家便是哥哥妹妹混着叫,分食一袋散装植脂末糖果。从同校到同班,一起升学、毕业找工作,结婚生子。只在最后一件大事,小怡慢了半步。
小镇里的人爱出国,越难越要出去。连做签证的中介,两个哥哥都找到同一人。成功案例多,拒签就退钱。哥哥做的是通过率更高的巴西签证,一到巴西,就乘船偷渡去阿根廷。郑阿姨不愿儿子冒出海的风险,宁愿多花十几万,坚持要做英国留学的假签证。那时小怡还在上海,满心为一年的实习期倒数,午间吃饭,听郑家妹妹说大哥面签没过,惹得郑妈妈大哭不止。小怡不知如何安慰,不免也有说英文大家都明白这事靠眼缘,要机会,郑大哥恰好碰上亚裔签证官,他假装上厕所,迎面仍然轮到他,只能紧张地吃下一张拒绝单。
回想起哥哥的进度,小怡装作无意问嫂嫂,才知道他刚递交签证材料。后来母亲发来短信,“通过”,三串惊叹的符号。
刘家的大儿子要去阿根廷了,大家都说。那天,父亲雇了戏班,在祠堂一遍又一遍地演出,哥哥充演一日主角,唱响了黄昏。
庆祝的酒席上,父亲拆开一包软中华,很虔诚地点燃第一根。感叹橘黄的烟丝真香,想起来,忙给儿子燃一支,右手搭靠他肩膀。父亲特意叫小怡请假回来,陪哥哥收拾行李,难得。大厅里坐满了人,赶来吃临行的饭,高粱酒碰杯,哥哥被灌得面红耳赤,支吾说不出答谢的话,只一个劲点头。
“出去要会吃,会喝,才好打点。”去过美国的表舅念叨。
哥哥不语。
“心意记住了,以后双倍返还大家。”父亲拍哥哥后背,热滚滚的,哥哥彻底伏趴在桌面。
嫂嫂抱杰杰下桌,喂他吃银鱼蛋羹。小怡沾了一身酒气,也来帮忙,嫂嫂咧嘴苦笑,笑这小孩不懂离别,胃口这么好。父亲乐得喝醉了,无边际地夸口,说等哥哥安定也把小怡带出国。小怡摆摆手,推说以后回村做个渔民,父亲只当是玩笑。
席上亲友,有不少经父亲挨家挨户叩门,为了凑齐哥哥出国的费用。他们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墨渍拉长,爬满人情债。郑阿姨自然是支持者,但她开的利息每月多出0.2厘,卖的是做生意的情谊,父亲还是应承下来。对着账,哥哥满面蜡黄,像闹饥荒的人。他的长跑才刚开始,拿签证是第一步,他还要赢过新来的东南亚学徒,同街区的华人超市。赢过移民政策,逐日难看的美金汇率,挣足够盖房子的钱再回国。
哥哥出国后的首个除夕夜,小怡和父母,嫂嫂一起看春晚,听《玫瑰人生》,看刘欢和苏菲·玛索拥抱,记得2008年他还牵过莎拉·布莱曼唱《我和你》,唱“同住地球村”。
要是地球真是一个村就好了,小怡暗想,不至于太远,也不至于太近。
后来,几乎在同一条客厅动线,小怡替死去的父亲支开大桌子,摆好流水席。当年的座上客,都来给父亲上香。村子纵然小,聚散还是寡淡,席间烟酒味弥漫。等人散尽,小怡发现嫂嫂和母亲在数钱,一张张翻过,红彤彤的。印象里操办白事并不收钱,小怡问了一句,嫂嫂抬头看她一眼,手中摩擦声不停。
后来,小怡才明白嫂嫂要买房子。不是母亲执意想要的郑阿姨家的自建房,而是嫂嫂在镇上看见的商品房,一梯三户,户型卖剩下的有108平方米,倒也合适四人居。有钱人都买这个户型,中介的话术,俨然也将她们归成一派。嫂嫂签字,听起来很满意。
母亲却一直抱怨:“到时候清明回来,你爸连家都找不到。”这句真令小怡神伤。她想起哥哥结婚前,嫂嫂面对二老说不介意没有婚房,母亲还笑称这是儿子的福气。
应对小怡的疑惑,嫂嫂的解释是没办法。只有一份钱,怪只怪他不努力。
嫂嫂又说:“当时要杰杰参加葬礼,说好给我们镇上买房。我又不是自己住,小孩读书不方便吗?天天接送的又不是你。”
她们在“努力”上存有微词,一个是为家,一个为自己。小怡知道,哥哥偷渡出国,争取移民,哪一环都有风险。嫂嫂没有给她辩驳的时间,一句接一句地说。
“你哥哥都在国外有了新家,我不能有吗?”原来远房亲戚告诉嫂嫂,丈夫刚开的超市出现一位新女孩,会在收银时用糖代替零钱,笑眯眯地省下一分一厘,捧着过日子的心情。
热。面对同样痛苦的表情,小怡脑后一股滚烫。她只好躲进房间,将门锁全紧闭。正午阳光轰烈,小怡靠角落阴影坐下,瞥见桌面支起八寸家庭合照,玻璃相框镀着淡金的天色。她愤然扇过一记耳光,相框落地摔得粉碎。
小怡点亮火柴,一根,映亮盆里渐堆起几张裁碎的相纸,玻璃残渣,替哥哥整理的笔记本,父亲出差带回的棉花熊猫。另一根,倒插于玩偶头顶,划开一团棉絮的焰火。她想倘若父亲在,定会狠狠骂上一顿,教哥哥持家应当如何。
再一根,点燃裁出的照片,燃起蓝色。火舌从最富氧的空隙间伸出,舔过哥哥的笑脸,作最后炙热的怀念。
夜里,墙壁那头传来哭声,小怡叹了口气,拢起衣服,穿过走廊枕在母亲旁侧。她伸出手,轻抚母亲的后背,哭声逐渐轻缓。她闻到自己指尖有熏剩的辣味,像是发过霉。
3
跨过铁桥,出租车司机停在村口,看小道开不进去,便嚷着要乘客下车。小怡只好拎着手电筒去找林昊。
台风变得更近,沙粒在空中卷出响声。菜畦前的水泥地全空了,这里原本是村民的乐园,白天晒小鱼,晚上聚拢吹夜风的老人,一圈又一圈讲闲话。小怡和杰杰一般大时,日日坐在菜圃间,贴着阿公的膝头,听他们谈起在厦门当兵,对岸金门的炮声和涨潮一样,响彻不停。
成功号的船讯,便是从夜晚座谈里听来的。
汛期天亮得急,先是起早的人,由窗望见海面开来一艘船,行速尤慢,银白色的点径直印在眼中。大家不敢靠近,取过望远镜,探见船身上“成功號”三个黑字。晚间聚会,一人一言便聊起来,有经验的渔人拍拍胸口,看长度和家用船差不多,断言不超6米。“啊呀,你看不到,有两层呢,舵轮这么大。”阿嬷虽未曾亲眼见,但从儿子处听来,也跟着用手比画。“里面可以藏人的。”
“不会又打过来了吧?”谁说起一句,使人遥想起炮声里炸断的尸首和沉船,难免惊惧,急忙唾了几口,忍不住骂那话茬的主人:“臭奶歹,没一句好听。”
“要我说,年纪大,鸡皮疙瘩走掉,死是迟早的事。”
“吃茶不会吃,讲这么多……”
一里一里地,船靠近码头,人们才看见其汽艇模样,尖三角式甲板,四周用铁栏杆围住。不像舢舨画有鱼和海浪,成功号就是蓝白两色,经层层粉刷,显出整齐的海洋文明。胆子稍大的年轻人跑进去看,才发现船舱空荡,里面根本没有人。
大概是养殖场没系紧,顺风飘来的,人们这样想。战争的威严落了灰,成功号变成小怡和同伴探险的去处,村民把船斜倚在码头石阶上,旁边倒扣一艘湛蓝色舢板,画着海鱼丰收,压一压成功号的怒气。八岁的小怡最爱当船长,她跳上甲板,大喊开船啦,转过头,看海岸在身后收紧。她想,以后还会有游客一船船远路而来,像英语画报上一样,看海、晒日光浴,人将日光融成调色盘。
终于等到当夜座谈会,小怡攀上阿公的背,拜托他带自己出海。
阿公却讲海哪里好看,船开到中央,四面是蓝色的水,白色的水,会晕船的水,生绿藻的水。水上有垃圾和塑料袋。小怡生气了,决定再也不陪阿公去菜园聊天,她拥有一艘出逃的船。
忽然,一束光聚在小怡身上,她拉回思绪,才发现林昊站在面前,也打着手电筒,身边另有一个女孩。
“我的实习生。”林昊说道。
他将手伸出来,让小怡握住,像一场友谊演奏会,女孩齐肩的短发被风吹乱,透出盐腥味。小怡引两人回家,女孩很热情地替她洗水果,葡萄一颗颗摘下放进铁盆,将实习生应有的紧张和热度用在每一处,反倒使小怡像个客人。
“阿姨呢?我很久没见她了。”看见林昊放于桌下的提盒,小怡脸露尴尬,只好说自己早和母亲分居了。她瞥见林昊眼中露出冷淡,像是在嘲笑她。小怡原本是为了照顾家人而辞职,没想到母亲并不需要她照顾。
小怡自然没有说谎。嫂嫂买房后,为了多陪杰杰,母亲便搬过去与嫂嫂同住。房子靠近中学,五百米内有菜市场,是镇上为数不多含小区公摊的商品房。哥哥寄来首付款,名字写上夫妻二人。交付时简至不能再简的装修,全交由嫂嫂,极快装满新生活的热情。
签字那天,母亲小声叮嘱小怡,朝北的房间留给她,虽然阴冷,但是暂时的,等到小怡结婚,该盖房子还是会盖。因着装修,母亲常常和设计师攀谈,家庭亲缘都问个清楚,母亲看男子年纪尚轻,工作稳定,和小怡还算相称,便长久留两个人在屋内装修。油漆袭面,心猿意马,没有人受得了,但男子每日身穿西装,站在旁边陪她闻,不时出门一趟,带回饮料和烟味。
“哪个是你的房间呢,怡怡?”男子问。小怡忍着无奈,指向拐角处幽暗的那间,男子轻哦了一声,说会替她装节能亮眼款吊灯,为自己能布置她的生活心欢、意足。他常用提问的口吻,使请求显得设身处地。问墙面漆成米黄色如何,能平和性情。下次见面,不如送她万年青,放在阳台可以招财。如果小怡也想结婚,两个人可以试试。
男子果真如母亲说的,不招人讨厌,头发蓄长软塌,还剩些孩子气。村委会工作清闲,小怡便答应周末陪他去看电影,爬山。偶尔也会想林昊在上海做些什么,从前的周末,两人最爱郊游,春天赏樱,秋日登山,远离家乡去拥抱自然的文明。或是在梧桐区典雅的老建筑前拍照留念,她听说这叫“打卡”,人声鼎沸,满是陪伴的乐趣,从不考虑日后照片都在心里打结。后来,她把照片都删光,只留下一个空荡的相册。
离开上海,小怡退回来,陪男子爬山,看电影。这段时间,无论是母亲,还是嫂嫂,忽然都感觉日子开阔,可以重振旗鼓,假象变得顺意,丝毫经不起打断。
装修落定那日,男子遣去工匠,邀她前来验收。小怡一进门就发现灯流璀璨,餐桌放着两瓶酒,朦胧望去真有家的心意。两人交碰,心思从酒杯内荡出,投下的影子在摇动。小怡不喜欢喝,男子却笑着往胃里灌,说自己从业这么久,第一次觉得收工是开心的。小怡就是他的收获,借装点慢慢显出明媚。像她这样,亲人在国外,见过大场面仍愿归家安顿的好女孩太少。小怡不说话,决意把酒喝完。
男子兴致勃勃邀她进房间,光线筛出星星点点,还可以调节,他在一旁转动按钮,由暖黄转至蓝光,这是德国进口的款式。小怡抬头凝视,接受由玻璃球铺洒的爱意,好比放大的星星置于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
忽然从背后被抱住,男子问她:“要不我们试试?”
就近订了一夜旅馆,小怡仰躺着,感觉被单上颗粒分明,她的眼睛将黄色灯管分作一块一块,细数那人用胡须擦过的区域,从双颊,到脖子,乳前。分不清何种心情,只感到身下一阵紧缩,男子趁亲吻间隙要她放松。进去了仍然吃痛,因僵硬被撑开的感觉。光线被压至眼皮下,她双手往后一撑,便着急退出来,男子再碰不到唇上那颗痣。
我们不合适,小怡一字一句通知他。男子着急辩解,凡事总有第一次。看着他急红的脸,小怡忽然歪过头,笑了起来,她想起林昊,左脸颊有块红色的胎记,总是消不掉。
4
房子装修完,小怡和男子也掐断了联系。她安心留在村委会工作,整理电子档案,记录自治活动,申请低保,繁琐又必须,反而唤起她对生活的热情。年底她要负责人口登记,一家一户地敲门,问名字,再一笔一画誊于问卷,记下家庭几口,为何只剩老人独居。村上多少户,她都数得清。村庄老得很快,常住人口比登记户籍少一半,每年底钱仍旧照发。银行账户也像一册户口本,总是存取用度,但户主不详,日子和钱一样迷迷糊糊便用完了。赶上医保政策更新,宣传之余,小怡最繁复的工作是教阿公阿妈用微信,发语音一定要等浪型声波出现,群聊需按绿键屏蔽。她发现自己对不爱的人比较有耐心,可以好言相劝,不执道理。
唯有母亲不领她的情,任凭邻居怎么说女儿乖,对老人又有耐心,母亲都不满意。踏过25岁,小怡还没结婚,于己是犯忌。电话里,母亲常抱怨自己入睡困难,小怡又不时给她熬煮中药,买安神补品。后来她才明白,真正让母亲失眠的,是那座总盖不起来的新屋。母亲常常描述郑家落成的过程,前后三个月,两层的石头古厝全拆掉,换作新瓦片,照亮众人洁净脸色,期待、欣喜、祝福,和仿古家具一样看不清原貌。母亲确实不解,儿子都送出国了,房子怎么还没盖起来。手执汇款单,母亲总是咂咂嘴,尽管很轻声,小怡总能听见。“不够啊,还是不够。”母亲说以前不是这样的,出国几年就赚到一座房子,现在怎么比不上在家做生意。小怡理解,大概是母亲实在怯于抱怨儿子,只好这样折磨她的耳朵。小怡是拆过的砖瓦,不够新与亮,填不满遗憾。但偏偏,母亲对自己又是没有期待的。
总在周末早晨,她与异国哥哥通话,想问那个女孩,话到嘴边又按下不提。她清楚做妹妹的职责,领域分在后方,于是关心生活和治安,瞥见新闻及时问候。只有一次,她说漏了嘴,哥哥反倒很坦然,只交代她不要惊动母亲,丝毫没有对嫂嫂的悔意。“女孩子我不会带回来,家里归家里。”小怡诧异于哥哥话含自豪,说明他为持家做的贡献,怎么听也不像醉酒会脸红的人。这大概也是异国的“赠礼”,于谋生中炸开一星火花,布局单属于他的新生活。恍惚间,她明白嫂嫂指着她鼻尖,说“这是你们家的事”,竭力将两家人划分开的毅力,因为怎么也划不开。护照是哥哥的护身符。
“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没有我们,你哪能这么安稳。”小怡撂下一句话,当即便挂断了,空荡荡的房间留下回声。
除了给杰杰挑选新学期文具,定期打扫房间,记录村庄日常事务,小怡不再有太多生活难题。返乡已是两年,生日那天,小怡给自己买了一个蛋糕,小票的蓝色油墨见证她的27岁。她正想将其收起,却发现抽屉老得拉不开。小怡猛力向外一抽,反而震倒坐在地上,柜子砸在地面,褶皱的纸片哗地如潮声席卷。她忍耐着痛,将张张展开,都是林昊寄的小票,从前的日子,从海上邮回来,逐渐失了色。
咖啡、甜点、毛绒玩具,原来与林昊分开后,她再也没有买过这些东西。小怡担忧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渐渐成为一个没有消费欲望和激情的人,不要结婚,不想看镜子里脱去衣服的自己,连老阿公摸她大腿都不情愿愤怒,固定开支是往渐空的冰箱内填新鲜蔬果。
卡住抽屉的元凶,是小怡13岁写过的满满一本日记。她翻开,上面记载讨厌和喜欢的人,才想起那时她爱张国荣,但未来得及买演唱会门票。还有两页,有关如何将村子建成阳光浴场,原来她还曾认真想过,日后该向谁申请经费。为此,以后要学城市规划,英语也要足够好,方便接待国外宾客。日记里的她对未来充满希望与安排,然而长大,她的许多念头在父母眼中,又变成开玩笑。但这日记提醒她,不是这样的,她还有一艘“成功号”。
“你们想不想看成功号,就在海边。”小怡看向林昊,开了口。
女孩在一旁连忙摆手,表示对台风的恐惧,再说了,船有什么好看的?只有林昊重重踢开椅子,站了起来。
“我跟你去。”
沉默地,两人离开家,往东南角走,越走越显出海面和更远处岛的轮廓。空气压薄,逼出紧张气氛,风里夹杂草籽翻过的味道。小怡不时侧过身看林昊的脸,对曾交换过爱字的人,小怡总期待他再说些什么,埋怨也好,调侃也罢,自己都会照单全收。她不知道,林昊也早养成等待的耐性。
走在码头上,所有系紧的船,不是为暂停,就是为出发。星象被雾气遮掩,银光水色。两个人的距离开开合合,剪出一道船行的痕迹。
到了,小怡指向那艘倾倒的成功号。小时候,每年她都报名替船画漆的活动,不为证明两岸关系,那只是她的仪式,她的周年庆。阴云下,船模糊掉边界,变得像纸,薄薄地透出光。小怡先踩上去,林昊很自然伸出手,曾经递文件的左手,戴戒指的右手,力量全压在掌心,要她把自己拉上去,去她小时候最爱的成功号。
甲板歪斜,两人站不稳,索性就着栏杆坐下。一滴落雨将她惊醒,小怡明白这警告。说些什么吧,她松开林昊的手,再说点什么吧?小怡劝自己。
第二滴雨落在头顶,旋涡处生出冷意。
“你跟我回上海。”对面的人开口说道。
“你妈妈不需要你,”林昊劝道,“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两人身影在甲板上对折,看似上弦月落至眼前。彼此只剩影子的距离,凹陷之处可以互补,林昊抱住她。
“跟我走吧。”
他们又松开,林昊径直扳过小怡的脸,用发白的双唇探寻她的痣。
小怡扭过身,再不敢回头。雨轰然应雷音而落,她停顿一步,自船向下看,泥地晃荡如海浪,她跳下船,拼命往家的方向跑,灯光都在眼中化开,于阖窗收衣锁门的纷纷声中她听到林昊的声音,大声念着自己的名字。
那艘船明明是出不了海的。她想,自己怎么还不明白。
——刊于《草原》2022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段文昕,1998年生,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作品散见《上海文学》《中国青年作家报》《少年文艺》《解放日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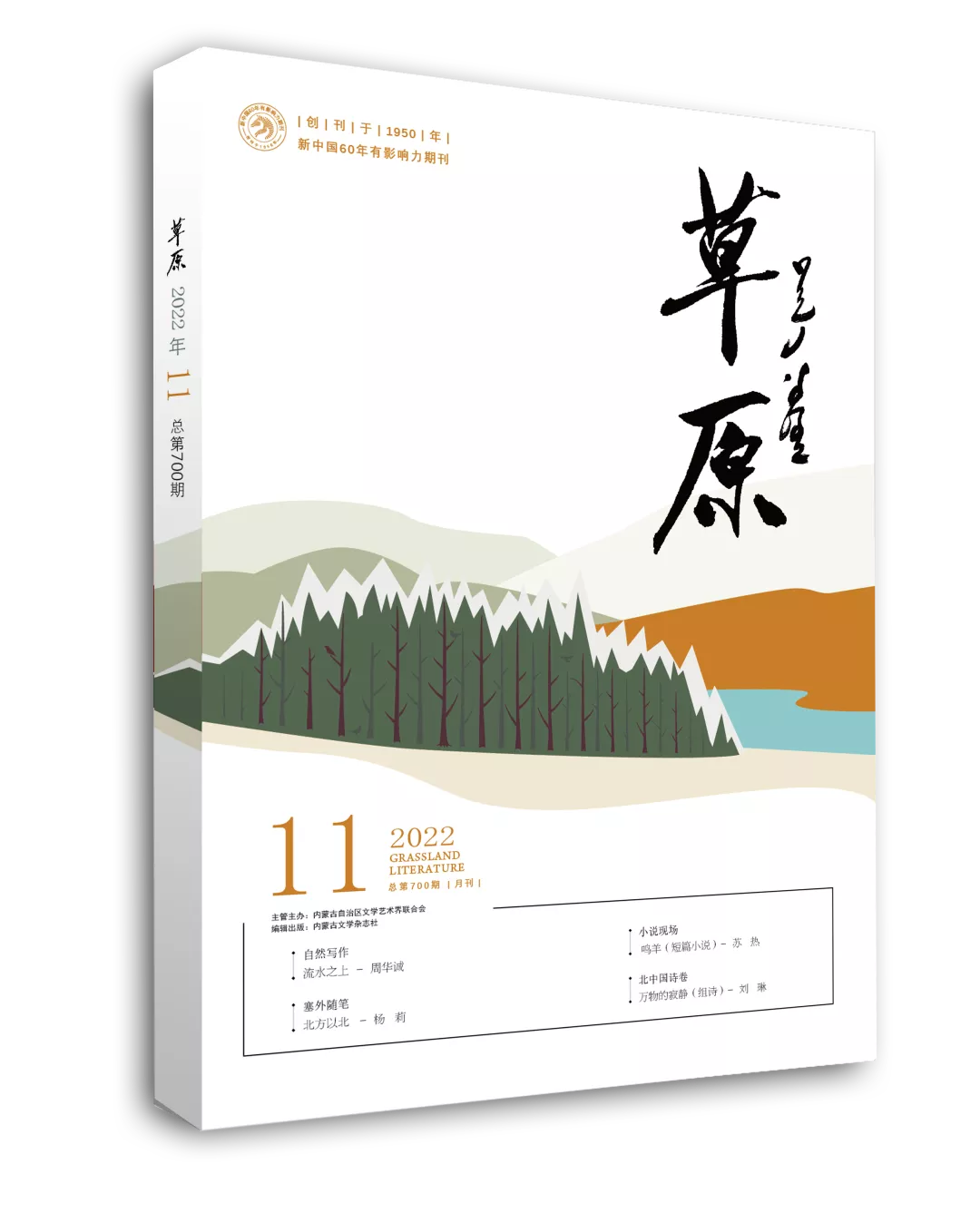
编 辑 | 塔 娜
初 审 | 高 阳
复 审 | 蒋雨含
终 审 | 阿 霞


来源:草原
https://mp.weixin.qq.com/s/mQmbGiPnbqVMuNDIVTGnww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