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勒比海潮汐里的古巴
加勒比海潮汐里的古巴
作者:陈双娥

古巴哈瓦那埃尔莫罗城堡
我心中的古巴,诞生于中国南方小镇的晨雾里。
那是大美河边一个个寻常的清晨。湿漉漉的雾气贴着河面爬行,漫过青石板,钻进木窗棂,给屋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朦胧的灰白。唯有厨房灶膛里跃动的火光,是这混沌中唯一清醒的亮色。灶台上,铸铁炉锅蒸汽升腾,传来米饭将熟时特有的、沉稳的噗噗声。
我的眼睛,时不时瞟向台桌上,那个陶瓷罐子。它比一般的罐子要高些,瘦长,印着我不认识的字和一片模糊的、像棕榈叶的图案。罐身有几处不起眼的锈斑,像岁月的雀斑。这是家里的“宝贝罐”,里面装着古巴糖。古巴糖甜得磊落又豪放,不像本地蔗糖,总是板结成一整块,需用刀背费力敲下,甜里带僵硬的吝啬。我打开罐盖时,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庄重,仿佛开启的不是糖罐,而是一个通往遥远世界的、香气馥郁的微型通道。
真正的仪式在于拌饭。滚烫的米饭盛入粗瓷碗,中心用筷子压出一个光滑的凹坑。我用那把专用的、边缘被磨得有些凹齿的小瓷勺,从盛猪油的青花瓷钵里,稳稳剜出一块。那猪油雪白,莹润,在常温下是凝固的脂玉,一旦触及灼热的米饭,便发出极其细微的“滋”声,瞬间塌陷、融化,化作一汪清亮而油润的泉眼,迅速向四周蔓延,浸润每一颗饭粒,使之泛起珍珠般的光泽。
然后,才是那神圣的一勺黄沙沙的古巴糖,从高处倾泻而下,落入那汪油脂的中心。奇妙的反应发生了:粗粝的糖粒遇到温热的油,并不立刻融化,而是先被包裹上一层亮晶晶的外衣,像无数微小的、裹了糖衣的金砂。筷子迅速搅动,金砂与玉粒、油脂开始了一场热烈而默契的舞蹈。最终,一碗朴素的白米饭,被点化成一种动人的琥珀色,油光潋滟,甜香扑鼻。
我捧着这碗“珍宝”,坐在门槛上,对着尚未散尽的河雾,吃得专心致志。猪油的丰腴滑润,与古巴糖那种独特的、略带颗粒感的、毫不迂回的甜,在口中交织成一种简单而极致的满足。
每一口,都暖和了胃,也似乎照亮了眼前灰蒙蒙的清晨。背着书包跑过湿滑的石板路时,肚子里暖烘烘,喉咙里便不由自主地溢出那支旋律:“美丽的哈瓦那,那里就是我的家。美丽的阳光照新屋啊,门前开红花……”
歌是老师教的,每个孩子都会唱。我们扯着嗓子,唱得响亮而又茫然。哈瓦那是什么?是像镇上供销社那样的大房子吗?红花是像河边野喇叭花那样吗?我不知道。但我的味蕾知道,哈瓦那,或者说古巴,是甜的,是金黄色的,是藏在那个神秘铁皮罐里、能兴奋晨昏的珍贵滋味。
家里另一种关于古巴的气息,则隐秘而浓烈。父亲的书桌抽屉深处,藏着一个扁平的、深棕色木盒。盒盖上的字母烫金已有些模糊。里面,在柔软的丝绒衬垫上,并排躺着三支雪茄。它们比父亲的卷烟粗壮得多,深褐色,油亮而紧绷的茄衣上,脉络清晰,像沉睡的、深色皮肤的手臂。父亲说的它叫金糖烟。它们被一层透明的玻璃纸谨慎地包裹着,如同沉睡的君王。
这木盒极少打开。唯有家中来客,是父亲极为敬重的人物时,他才会在饭后,洗净双手,用一把小银剪,极其仔细地剪开一支雪茄的尾部,然后划燃一根长长的火柴,并不急于点燃,而是让火焰稳定后,才缓缓转动雪茄,让茄衣均匀地熏烤、点燃。那时,一股我从未在其他烟草中闻到的气息,便会沉沉地弥漫开来。它不似卷烟那般轻浮呛人,而是一种更为丰厚、复杂、带有焦糖、皮革、泥土和某种厚重木质混合的香,甚至有一丝危险的诱惑力。
客人通常只是浅尝辄止,神色郑重,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烟雾缭绕中,他们偶尔会谈及一些对我而言很深奥,或者是根本听不懂的事情。很多时候,客人的眼神会变得悠远地说:“好东西啊,就是劲儿太冲。”
一次,我按捺不住好奇,趁大人散去,烟灰缸边那支雪茄尚未完全燃尽,偷偷凑上去,猛吸了一口那残留的、青蓝色的余烟——
“轰!”
仿佛不是气体,而是一团有形的、滚烫的、带着无数微小荆棘的固体,猛地撞进我的喉咙,粗暴地刮过气管,直冲肺叶。我猝不及防,被那强大而陌生的力量噎得双目圆睁,随即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咳嗽,眼泪鼻涕瞬间汹涌而出,整张脸憋得像块红布。那不仅仅是呛,那是一种宣告,一种来自遥远热带土壤的、蛮横而原始的植物力量的示威。
古巴,在我童年的认知版图上,就此彻底分裂:一半是光明、直接、抚慰身心的甜;另一半,是黑暗、复杂、极具冲击力的烈与呛。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那个名叫“古巴”的、遥远而矛盾的想象。
几十年光景,如大美河的流水,不舍昼夜。我离开了小镇,走过了许多比“大美河”更宽阔的江河湖海,见识了比猪油、古巴糖拌饭更繁复的滋味。生活教会我节制,糖分成了需要谨慎计算的指标,那碗金黄油亮的童年滋味,被封存为一种不合时宜的、略带负罪感的怀旧。雪茄的气息,则彻底消失在空气里,连同父亲和那些谈论遥远国度的客人们,嘴里吐出的金糖烟圈。
然而,某段旋律的尾音,会像河床底部的卵石,在某些毫无防备的时刻,被记忆的流水冲刷出来,突兀地硌在心头。在超市货架看到各色沙糖时,在电影里听到拉丁音乐时,甚至在某个疲惫的黄昏,闻到类似旧木头与干草混合的气味时……“美丽的哈瓦那……”那调子便会自动哼起,像一段无法删除的生理记忆。
直到那个加勒比海的午后,机舱门打开,一股裹挟着海盐、暖风、浓烈植物腥味,以及某种淡淡铁锈味的空气,猛地拥抱了我。阳光不是照射下来的,而是像融化的金色糖浆,从湛蓝得近乎失真的天穹倾泻而下,粘稠、厚重,带有实实在在的重量和温度,瞬间在我皮肤上镀了一层微烫的金箔。

古巴哈瓦那的切·格瓦拉壁画墙,位于哈瓦那革命广场附近
哈瓦那,我万里之外的所在,就这样毫无过渡地撞入眼帘。
首先征服我的,是色彩,以及色彩在变幻中展现的惊人生命力。这哪里是一座城市,这分明是一片被飓风遗忘在时间海滩上的、巨大而斑斓的贝壳遗骸。殖民时代遗留的建筑,骄傲地展示着它们曾经的奢华:罂粟红、孔雀蓝、芒果黄、薄荷绿……每一面墙都像一声嘹亮而绝望的呼喊。
然而,海风与时间是最无情的剥蚀者。墙皮大片地剥落,露出底下砖石粗糙的、病态的肌体;精美的石膏花饰残缺不全,如同美人溃烂的疮疤;鲜艳的油漆在漫长的曝晒下,褪成一种苍白的、幽灵般的粉彩。雄伟的廊柱下,晾晒颜色俗艳的衣衫;雕刻天使的阳台栏杆锈迹斑斑,上面垂挂几盆营养不良的天竺葵。漫步其间,每一步都踏在时光的褶皱里,每一瞥都能与历史撞个满怀。

哈瓦那的圣弗朗西斯科广场
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衰败,却衰败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生机勃勃。就像一支激昂的进行曲,偏偏用走了调、生了锈的乐器来演奏,反而迸发出一种荒诞的、令人心碎的力量。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寻找“孩子们午后在革命广场踢足球,皮球会掠过切·格瓦拉巨幅壁画;黄昏时分,海明威常去的La Bodeguita del Medio酒吧里,朗姆酒与查查舞曲依然沸腾,墙上泛黄的签名簿上,海明威那句“我的莫吉托在La Floridita,我的达伊基里在这里”留下的传奇。

五颜六色的老爷车
在这片凝固的、跌宕的彩色乐章中流动的,还有那些声名赫赫的老爷车。它们不是博物馆里供人凭吊的标本,而是这座城市仍然跳动着的、衰老而亢奋的心脏。五颜六色的庞然大物——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产凯迪拉克、福特、雪佛兰——喘着粗气,哐当作响地行驶在崎岖不平的石板路上。它们的颜色比建筑更大胆:电光紫、火焰橘、荧光粉……司机们似乎把所能找到的所有油漆,任性地泼上车身,以一种近乎挑衅的狂欢态度,对抗着无处不在的锈蚀。
我坐上了一辆粉蓝色的敞篷“战舰”。司机是个精瘦的老人,名叫米格尔,牙齿掉了几颗,笑起来黑洞洞的,但眼睛亮得像少年。
“她叫‘卡米拉’,1957年出生,比我老婆还了解我!”米格尔用力拍打方向盘,引擎发出一阵类似咳嗽的轰鸣,车子猛地向前一窜。“零件?哈!俄罗斯的、中国的、自己用锉刀磨的……她能跑,就是奇迹!是我们在养活这些老家伙,也是这些老家伙在养活我们。”
车子驶过海滨大道,蔚蓝的加勒比海在右侧铺展到天际,左侧是连绵的、伤痕累累却色彩飞扬的建筑。海风猛烈,几乎吹走我的太阳镜。
米格尔却张开嘴,迎着风唱起一首欢快而沧桑的歌,歌声断断续续,融化在发动机的噪音和海浪声里。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这种在我的国家早已报废的车辆,在这里却是美丽的“移动废品”。它不是什么浪漫怀旧,而是一种坚韧的生存哲学。用尽一切办法,让过去的躯壳承载当下的生活,在匮乏中创造绚烂,在禁锢中寻求驰骋。这本身就是一曲悲怆而昂扬的“哈瓦那之歌”。

白色的敞篷“战舰”
为了寻找童年那口“呛”的源头,我走进了哈瓦那郊区一家雪茄工厂。外面的世界色彩喧嚣,里面却是另一个宇宙:昏暗,寂静,只有高窗投下几束光柱,照亮空气中缓缓浮动的、金黄色的烟草尘雾。浓烈的、几乎是固体般的香气包裹过来,那是我记忆深处的气味,但浓度更浓的烟草叶、发酵的甜、烘烤的坚果香、隐约的胡椒辛,还有陈年木头与皮革的底蕴。
工人们一排排坐在长条木凳上,每个人面前堆着不同颜色、质地的烟叶。他们的手指粗壮,动作却精确得像外科医生。取叶、展平、去梗、叠放、卷制、修剪、定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沉默而迅捷,几十道工序在几分钟内于指掌间完成。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专注得近乎麻木,只有眼神偶尔掠过手中的“作品”时,会闪过一丝极细微的、匠人特有的掂量与满意。
我试图与一位年长的卷制师傅交谈。他叫赫苏斯,手指被烟叶染成了深褐色。“一辈子了,”他用简单的英语单词,配合手势说,“我父亲,父亲的父亲……都在这里。雪茄,不是烟,是时间。”他拿起一片深色的茄衣烟叶,对着光,让我看那细密如网的叶脉。“阳光,土壤,雨水,人的手,还有等待……很多很多的等待,才变成这样。”他将其熟练地裹上已经成型的茄束,动作轻柔如抚摸婴儿的肌肤。“你抽过?呛?”他咧开嘴笑了,露出被烟草熏染的牙齿,“好雪茄,第一口是甜的,像糖。后面的力气,是生活给的。”
生活给的力气。这句话像一记轻轻的叩击,敲在我心上。几天后,在巴拉德罗旅游区那片被精心修饰过的、蓝得不真实的海滩上,这句话找到了它最具体的回音。
这里的古巴,是另一个版本。全包酒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阳光、沙滩、无限量供应的食物和饮料,殷勤周到的服务生。

全包酒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
我们沉浸在一种被精心安排的、无忧的惬意中。直到我注意到她,那位总是主动负责我们的服务员,一个叫莉亚的年轻女人。她有着蜜糖色的皮肤和一双仿佛不知疲倦的手,笑容标准,但眼睛里有一种其他服务员没有的、过于锐利的观察力。她会记得我儿子喜欢莫吉托和哪款鸡尾酒。会在我小孙女坐在婴儿车上时,下意识地伸手虚护一下。
混熟之后,一个午后,泳池边人声嘈杂,她趁着帮我儿媳捡起掉落的玩具的间隙,用很快的语速,低声而清晰地说:“女士……你们离开那天,如果……如果宝宝有些穿小了的、不打算带走的衣服和鞋子……我的女儿,刚满一岁,和他差不多大。”
她的话语流畅,显然在心中预演过无数遍。说完,她立刻抬起头,恢复那个灿烂的职业微笑,补充道:“当然,也可完全不用介意!祝您下午愉快!”
然后迅速转身,走向另一张需要清理的桌子,背影挺直,步伐轻快,仿佛刚才那句轻轻的请求,只是一句关于天气的闲聊。
加勒比海的阳光依旧炽烈,晒得我皮肤发烫,心里却陡然一凉,随即泛起一阵复杂的酸楚。莉亚那迅速隐藏起来的期盼眼神,像一把锋利的薄刃,划开了度假天堂那层光鲜的薄膜,让我窥见了其下坚实而粗粝的地基。在那些色彩斑斓的老爷车、醇厚名贵的雪茄、游客尽享的朗姆酒背后,是普通古巴人需要动用“人情关系”才能进入旅游区工作、为了一包孩子旧衣而小心措辞的日常生活。
那首儿歌里“美丽的阳光照新屋”,此刻有了双重的意象:既是眼前这酒店簇新的别墅,也是哈瓦那旧城里,那些虽然斑驳却依然有人顽强生活的“新屋”。

哈瓦那革命广场
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我执意要独自去哈瓦那老城走走。穿过喧闹的武器广场,避开招揽生意的乐手和画家,我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阳光在这里被切割成狭窄的光带,照着一扇褪色的蓝门。门边坐着一位年迈的黑人妇女,穿着一条颜色模糊的裙子,安静地剥着豆子。她的面容像风干的胡桃,布满深邃的纹路,眼神平静地望着虚空。
我停下脚步,对她微笑。她缓缓抬起头,也回以一个微笑,露出光秃的牙床,然后用西班牙语轻声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懂,但觉得那语调温柔。
就在那一刻,毫无征兆地,心底那首沉寂已久的歌,再次完整地、无声地响彻我的脑海。而这一次,它自动配上了全新的画面:不再是童年碗里那片单薄的金黄,而是哈瓦那废墟上鲜艳的颓废,是老爷车轰鸣中司机缺牙的笑,是雪茄工厂里工人被染褐的手指,是酒店服务员快速说话时轻颤的睫毛,是眼前这位老妇人沟壑纵横的脸上,那抹平静如深湖的笑意。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就是我的家,美丽的阳光照新屋啊,门前开红花……”
我忽然泪流满面。
我终于来到了糖的彼岸,却发现这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甜。古巴用它浓烈到刺目的色彩、顽强到心酸的生存、呛烈而又回甘的醇厚,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梦想之地,从来不是童年想象中那个无菌的、单向度的蜜罐。它是所有滋味的总和,是所有时光的层叠——甜与苦,亮与黯,兴盛与衰朽,困顿与尊严,历史的重负与生命不息的欢歌,全部炽热地、不加调和地糅合在一起,像一支上好的雪茄,第一口或许是期待的甜,但那之后磅礴而来的、复杂而深邃的力道,才是生活与土地本身的真相。
那“红花”,或许从未在门前规整地开放。但它一定绽放在斑驳的阳台上那盆倔强的天竺葵里,在米格尔迎着海风哼唱的跑调歌声里,在赫苏斯手中那支即将封藏时间的雪茄里,在莉亚想象女儿穿上中国服装时闪亮的眼眸里,也在这位剥豆老妇人面对过客的、平静的微笑里。
我带走了一小包真正的古巴糖,黄沙沙的,和童年记忆里一模一样。也带走了几盒雪茄,不是昂贵的品牌,只是普通小店里的寻常货色。它们并排放在我的书架上,不再仅仅是食物或物品。它们是一个坐标,标记我从一碗拌饭的甜,走向一个辽阔、复杂、充满生命力的真实旅程。糖的彼岸,并非甜的终结,而是我终于尝懂了,那份甜所得以诞生的、全部的苦涩、呛烈与坚韧的土壤。这滋味,让我在往后的许多个清晨,面对自己简单清淡的早餐时,心中能升起一份更加沉静、丰厚、充满理解的暖意。
“潮汐去还,谁所节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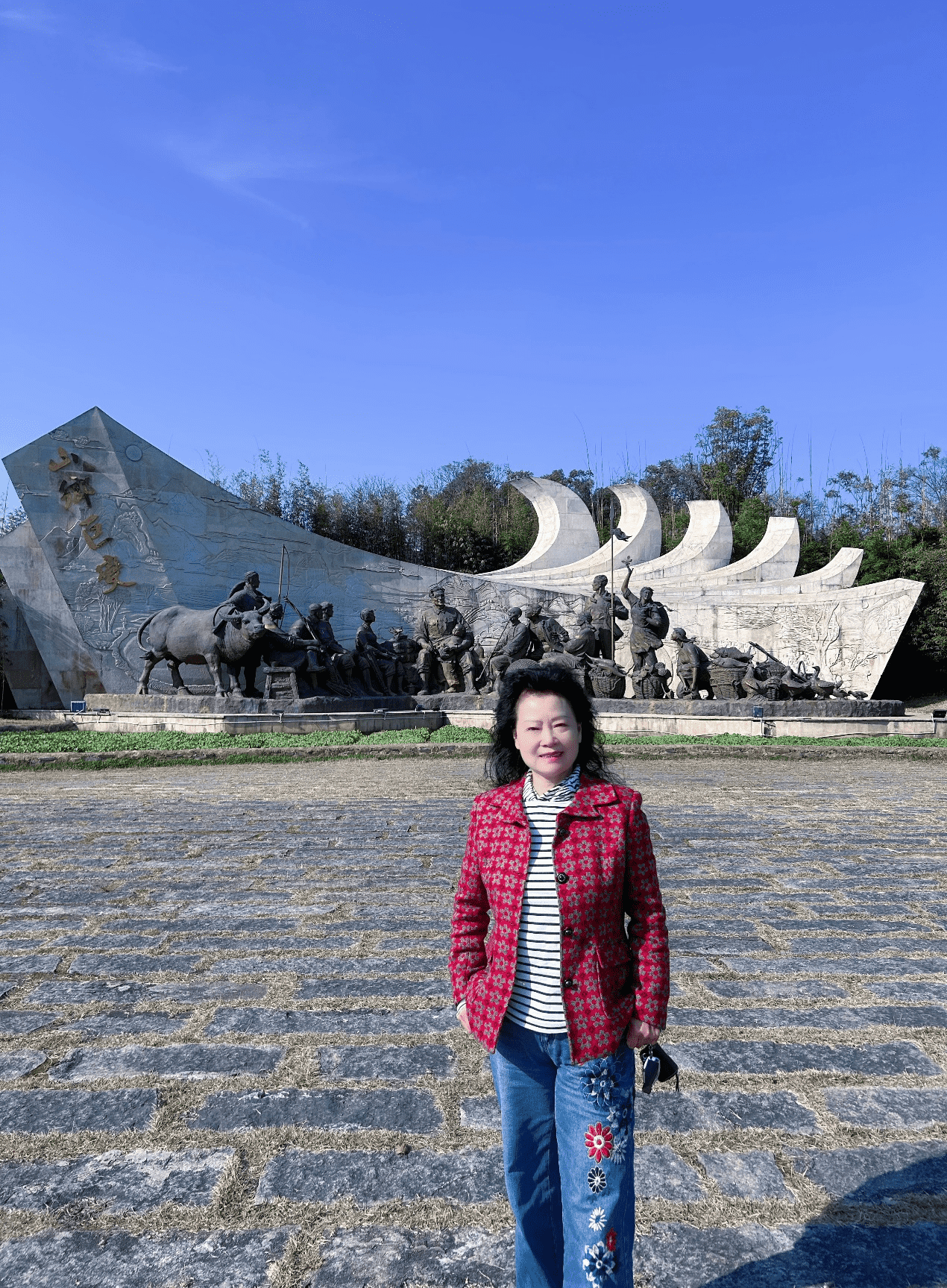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陈双娥,1957年生,湖南汉寿县人,毕业于湘潭大学,国家二级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发表处女作《会计之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反绑架》;长篇纪实小说《大追捕》;长篇儿童小说《险走洞庭湖》;法制文学作品集《权与法的较量》《钱与法的碰撞》《义与法的冲突》《生死赌注》《生死抵押》《生死游戏》。《义与法的冲突》获公安部第四届金盾文学奖三等奖、湖南省第二届金盾图书奖一等奖。新作《柚子念》《母亲的目光永远是最温柔的导航》《我知道你今天会来》《加勒比海明珠之夜》《老家在时光里酿成了诗》《铁甲村正向你走来》《我还在路上》等在 “红网”“作家网”“正扬网”“走向”和《湖南日报》《潇湘晨报》《华侨新报》《华侨新视野》发表后,获得广泛赞誉。
(注:文中照片由陈双娥、杨远新提供)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