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歌同行
与歌同行(随笔)
作者:董勤生
秋天的午后总带着点懒怠,阳光穿过窗帘缝,在手机屏上投下一道细窄的光带。本是随手点开短视频,想打发一段零碎的时光,却没成想,李小萌开口唱出那曲《探清水河》的瞬间,指尖的滑动忽然顿住 。整个世界好像被按下了慢放键,唯有她的嗓音携带着老北京胡同里的槐花香,不稠不稀,正好漫过耳际。
那纯正的北京琴书调子,不是时下流行的快节奏,没有电子乐的轰鸣,也没有刻意炫技的转音,就只是“桃叶儿那尖上尖,柳叶儿那遮满了天”,一字一句都踩着胡同里的青石板路。她的声音清得像刚从什刹海取上来的水,带着点凉,却又暖得熨帖。比如“日思夜想的六哥哥”那句,尾音轻轻往上挑,不是撒娇,是姑娘家藏在帕子里的心事,软乎乎地飘出来,落在人心里就化了。旋律更妙,京胡的弦一拉,像胡同里蹬着二八自行车的大爷晃着车铃,一顿一扬都踩着日子的拍子,板鼓敲得 “咚咚” 响,不慌不忙,正好把老北京的烟火气都敲了出来。就这么坐着,手机搁在膝头,听她唱完一段又一段,等回过神时,窗外的阳光已经歪了,原本只打算 “听两句” 的,竟偷偷溜掉了半个下午。
听着听着,就想起这些年某些变化。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越来越喜欢一些过去讨厌的北方戏曲了。小时候总觉得京剧节奏太慢,京韵大鼓格调显得沉郁。听《苏三起解》里 “苏三离了洪洞县”,一句能拉老长,急得我总想替苏三把话说完;听骆玉笙唱京韵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那低沉的调子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如今再听,倒觉得这份 “慢” 里藏着大乾坤。
传统京剧里的吟唱,从来不是急匆匆的赶路,是闲庭信步的琢磨。比如梅派的《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 那句四平调,梅兰芳先生的传人唱起来,声音像云一样飘,绕着戏台的梁子转,不是飞,是游,每一个转音都像贵妃手中的团扇,轻轻一扇,就带出了大唐的风。京韵大鼓更甚,骆玉笙的嗓子像老紫檀木,敲一下能发出绵长的回响,唱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时,那调子不是喊,是沉,沉得能砸进历史里,让你跟着想起老北京城墙下的悲欢。这些戏曲里的不急不慌,像极了原始深林中的白发樵夫 —— 他背着柴捆走在腐叶上,脚步没半点急燥,手里的柴刀偶尔敲在树干上,“笃” 一声,倒比戏里的板眼还准。你跟着他走,听他偶尔哼两句不成调的曲子,走着走着,就走进了一片苍茫 。但没有苍凉,是岁月沉淀后的开阔,好像所有的急脾气、烦心事,都能被这慢调子磨得软下来,跟着白发樵夫的脚步,一步一步踏进岁月的深处。
可年轻时候,我偏不喜欢这份 “慢”。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我揣着录取通知书,来到黄河故道旁的一座城市求学。一到秋冬季,故道里的风沙就裹着土腥味扑过来,打在脸上像没磨过的砂纸,连教室的窗户都灰蒙蒙的。风一吹,“哗啦哗啦” 响,像谁在窗外扯着嗓子喊。唯有夏天不一样,一场暴雨过后,空气里满是树叶和着泥土发酵的甜香,连故道里的缓慢流淌的河水都清澈了,河边的杨树林里,叶子上挂着的水珠能亮一整天。
那时候我总爱早起。天刚一亮,就揣着《古代文学》走出校园,踩着沾了露水的青草,往小河边的树林里去。晨雾是从河水里蒸出来的,薄得像纱,沾在睫毛上凉丝丝的,一眨眼睛就零落成小水珠。找棵粗点的槐树靠着,开始背诵《诗经 · 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嘴里念着,眼睛盯着河面,看着雾慢慢散开,太阳慢慢爬上来,把光洒在水珠上,树叶上的亮斑就跟着晃,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就在我念到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时,忽然学校隔壁省运输公司六十六车队的大喇叭响了起来 。那是 “每周一歌” 的栏目,前奏刚过,一个甜美的女高音就飘了过来:“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啊,请喝一杯茶!”
那声音太干净了,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泉水,带着井壁的清凉,顺着耳朵往下流,流到胃里时,连早上背书时的口干舌燥都化了。手里的书忘了翻,耳朵跟着那调子走,听她唱 “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甜又香”,连空气里都好像飘着茶叶的清香。那时候广播里的歌多半是 “雄赳赳气昂昂” 的硬气,要么就是 “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激昂,突然冒出这么软乎乎、带着南方茶山水汽的调子,就像在满是糙面馒头的桌上摆了碟白糖糕,让人忍不住多尝几口。后来才知道,这是《请茶歌》,因为带着井冈山的红色基因,才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一周 。可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基因,只知道每次听到这歌,就像在闷热的夏天喝了碗冰镇绿豆汤,浑身都透着爽利。
《请茶歌》之后,广播里的调子渐渐软了。没过多久,就听到了李谷一的歌。她唱《乡恋》时,声音里带着股 “气”,不是喊出来的,是叹出来的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那口气绕着 “身影” 转,像春风拂过麦田,麦浪都跟着晃。之前听的歌,多半是 “直来直去” 的,调子是调子,词是词,可李谷一的歌不一样,她的声音里有 “情”,唱《难忘今宵》时,“无论天涯与海角”,尾音轻轻落下来,像朋友在耳边说悄悄话,暖得人心头发热。后来才明白,李谷一的出现,不是偶然 —— 那是一个艺术新时代的标志,就像冬天过后的第一缕春风,吹醒了之前紧绷的旋律,也吹开了人们心里对 “抒情” 的渴望。
可真正让我觉得 “时代变了” 的,是邓丽君的磁带。在那之前,偶尔能在半导体收音机里拧到 “敌台”,里面会飘出邓丽君的歌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信号忽强忽弱,像隔着一层棉花听人说话,还得竖着耳朵防着旁人听见,生怕被人说 “听靡靡之音”。可后来,不知是谁先把邓丽君的磁带带到了学校,再后来,连乡村中学的供销社里,都能偷偷买到她的磁带了。
那时候我刚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小卧室,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因为我有一台二手的录音机,还有好几盘邓丽君的磁带。周末的时候,同事里的几个单身青年会凑到我屋里,有人带一瓶啤酒,有人揣一把炒花生,我把录音机放在桌上,按下播放键,“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的调子就飘了出来。
邓丽君的声音太软了,像刚晒过太阳的棉被,裹着人就不想动。她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不是直接的表白,是娇嗔的询问,每个字都像撒了把糖,甜得人心里发颤;唱《我只在乎你》时,“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调子轻轻的,带着点委屈,却又满是依赖,听的时候总想起自己的心事 —— 那时候刚谈恋爱,跟对象隔着几十里地,只能靠书信联系,每次听这首歌,就好像邓丽君在替我说话,把心里的想念都唱了出来。啤酒瓶碰得 “叮当” 响,邓丽君的声音混着啤酒的麦香,连窗外的月光都变得软乎乎的。那时候觉得,日子就该这么过 —— 有歌听,有朋友,有盼头,哪怕住的是不到十平方的房子,也觉得满屋子都是亮堂的。
后来,国内的音乐也开始 “不一样” 了。先是杭天琪的《黄土高坡》,一开口就震住了人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那声音里带着股冲劲,像黄土高原上的风,裹着沙粒,刮得人心里发颤。那时候日子还紧,买块肥皂都要算着用,镇里的路还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可《黄土高坡》里的 “喊”,不是怨,是较劲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唱的是多少人心里的劲儿啊。我在电视上看杭天琪唱这首歌,她穿着红色的上衣,头发甩得高高的,眼神里满是倔强,好像在跟生活叫板。那时候觉得,这歌就像一把火,能把人心里的憋屈都烧没了,听着听着,就想跟着她一起喊,喊出心里的劲儿。
再后来,就听到了崔健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那是摇滚,跟之前的歌都不一样 。 没有甜美的调子,没有抒情的歌词,只有崔健抱着吉他,甩着头发,嘶吼着 “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飞不高”。那声音里满是迷茫,却又满是不甘,像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看着偌大的世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可又不想停下脚步。那时候我已经在小城定居了,有了家,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安稳,可心里偶尔也会有 “飞不高” 的失落 —— 想换个好点的工作,想让家人过得更好,可现实总有些牵绊。每次在电视上看崔健唱这首歌,都觉得心脏跟着跳得快,好像自己心里的那点不甘,都被他喊了出来。虽然没机会去首都的万人剧场感受那种氛围,可光是在电视上看,就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还是朱哲琴。朱哲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第一次听是在收音机里,前奏刚响,就觉得自己站在了芦苇荡里 ,到处都是鹤鸣,水鸟掠过水面,“哗啦” 一声,溅起一圈涟漪。“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朱哲琴的声音一出来,就像丹顶鹤的翅膀掠过蓝天,清凌凌的,带着点空灵感,能把人从柴米油盐的日子里拉出来。她的嗓子高,却不尖,唱到 “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 时,声音慢慢往上扬,像鹤群飞向云端,带着点悲壮,又带着点圣洁。我总想起歌里的那个女孩,为了救丹顶鹤掉进沼泽,那么年轻的生命,却跟芦苇荡、丹顶鹤永远留在了一起。每次听这首歌,都觉得心里软软的,好像自己也变成了芦苇荡里的一缕风,陪着那些丹顶鹤,陪着那个女孩。
除了国内的歌,还有一首外国歌,我记了一辈子。那是日本电影《人证》的插曲《草帽歌》,“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乔山中的旋律一出来,就带着点涩,像秋天的柿子,甜里裹着酸。那声音是叹,叹时光,叹离别,叹那些回不去的日子。“突然狂风呼啸,夺取我的草帽耶!”歌者吟唱到此,突然转入高音,更是母爱失落无法追寻的哭泣和哀嚎,那是一种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痛,听者的灵魂则渐渐被抽走,落下的就是一腔空壳。何为长歌当哭?此歌便是。我第一次听是在邻居家的黑白电视上,电影里的男主拿着草帽,站在悬崖边,调子慢慢飘出来,连电视里的雪花点都好像跟着静了。那时候我刚失去母亲,母亲生前总戴着一条白地蓝花毛巾,夏天在地里干活,秋天在院里晒玉米,那毛巾陪着她走过了多少日子。后来母亲走了,毛巾也不知丢到了哪里,每次听《草帽歌》,就想起母亲的样子,心里空落落的,却又觉得温暖 —— 至少还有歌,能帮我记住那些日子。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片段,杨子荣唱《打虎上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熟悉的调子一出来,我手里的茶杯都差点没拿稳。五十年前,我还是个孩子,家里的磁石喇叭挂在墙上,天天放这首歌 —— 早上放,中午放,晚上也放,那时候觉得吵,嫌杨子荣的调子慢,嫌京胡的弦拉得刺耳,总想把喇叭的开关拧小。可现在再听,却觉得亲切得不行 —— 杨子荣的长吟像老熟人敲门,“吱呀” 一声,门开了,小时候的日子就涌进来了:我趴在门槛上写作业,喇叭里的调子跟着笔尖走,妈妈在厨房做饭,烟筒里的烟飘得慢悠悠的,邻居家的小孩跑来喊我去玩,我们追着跑着,笑声混着喇叭里的歌,飘得满院子都是。
可高兴劲儿没过,心里又有点酸。现在的年轻人,爱听的是电子乐、说唱,节奏快得像打鼓,歌词也多半是 “潮流”“个性”,很少有人再听京剧了。上次孙女来,我放《打虎上山》给她听,她皱着眉头说 “爷爷,这歌太老了,不好听”,转身就拿出手机,放起了我听不懂的调子。我不怪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就像我们小时候不爱听京剧,他们现在也不爱听我们的歌。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 这么好的调子,这么有味道的词,怕是以后听的人会越来越少了。这种慢节奏的音乐,好像只剩下我们这些老人还当个宝,因为我们经历过那样的日子,能听懂歌里的故事,也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回忆。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没必要难过。人生不就像一张唱片吗?每个时期都是一段曲子,有激昂的,有舒缓的,有甜的,有涩的,可哪一段都少不了,哪一段都有它的精彩。年轻的时候,爱听《请茶歌》的甜,爱听邓丽君的软,那是因为我们心里满是憧憬,满是热情;后来爱听《黄土高坡》的冲,爱听崔健的吼,那是因为我们在为生活奋斗,在为梦想较劲;现在爱听京剧的慢,爱听《草帽歌》的涩,那是因为我们开始回忆,开始懂得珍惜。
没有哪个时期的喜好是 “错” 的,也没有哪个时期的人生是 “差” 的。就像我现在,午后晒着太阳,听李小萌的《探清水河》,听杨子荣的《打虎上山》,偶尔也会听孙女放的流行歌,虽然听不懂,却也觉得热闹。音乐就像一条河,陪着我从年轻流到现在,以后还会接着流,它不会嫌弃我老,也不会催促我赶时间,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我,走过每一段日子。
与音乐同行,听着歌,想着事,念着人,日子就不会孤单,也不会乏味。不管是过去的歌,还是现在的歌,只要能让心里暖,能让日子甜,就是好歌。至于时光嘛,慢慢来就好,反正有歌陪着,每一段都值得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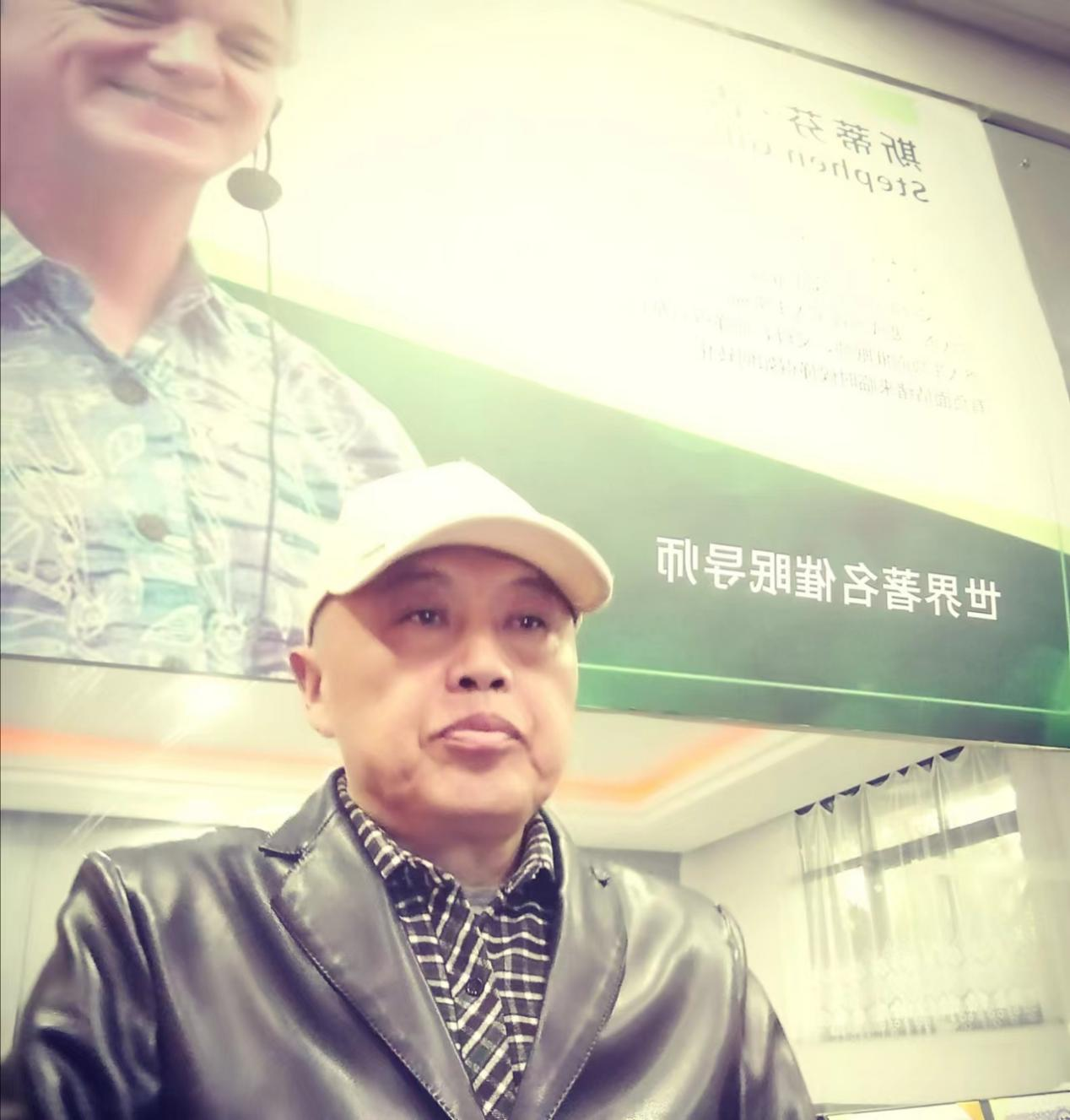
作者介绍:董勤生,江苏淮安,退休中学教师。早年有散文、小说见刊于《小说报》(吉林)《伊犁河》(新疆)《崛起》(淮安)《扬子晚报》《淮安日报》《江苏教育报》等刊物。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