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林里听广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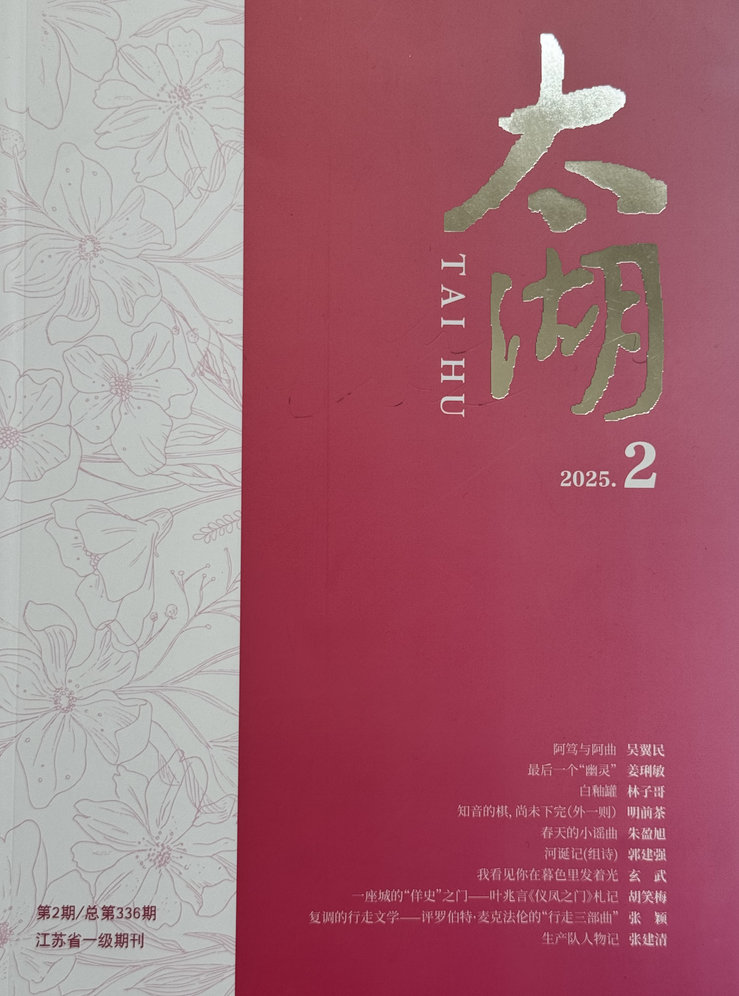
大森林里听广播
作者:柳邦坤
一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7点整。”“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这是我儿少时几乎天天都能听到的声音。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广播长大的,广播伴随我们度过了寂寥岁月。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文化生活贫乏。家在大森林里,林业电影放映队巡回放映,要一个月左右才能轮到一回,盼着电影放映队来,犹如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当时林区小镇和我就读的子弟学校,有文艺宣传队,会排练文艺节目,演出也不是经常有,一般集中在春节前排练、演出。地区和县上的专业文艺团体,各来过大森林演出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听广播就成了主要娱乐和求知方式。
听广播,离不开收音机和广播喇叭。收音机,也叫戏匣子,广播喇叭即安装在家家户户的扬声器,也俗称小喇叭,安装在街道上的大扬声器也俗称大喇叭。我的童年时代,收音机绝对是奢侈品,不记得谁家有收音机。那时较为普及的是广播喇叭,第一次听广播是在孙吴县城,我大概五六岁,随父母从几十公里外的林区小镇辰清来到县城,住在一位父母的朋友家里,早晨还在梦乡里,就被歌声吵醒,那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问了父母,才知道那歌声是从窗户上面的一个匣子里传出来,记得播放的歌儿是《社会主义好》。
后来,父亲开发新林区,工作调动到爱辉县,仍在大森林里。1960年代末,林区小镇办起了广播室,家家户户都接上了小喇叭,街道上安有大喇叭,供路上的行人收听。广播里主要是播通知,放样板戏、歌曲的唱片,也播放黑河区文工团、爱辉县评剧团来演出的录音,演出录音能播放好久,因此记住了文工团、评剧团许多演员的名字,如金宝骥、陈圣中、孟西娣、袁世纪、胡占利、姚淑琴、乔福宝等,听说文工团还有一位知名歌手孟梅,那次她没有来。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的老师孙英珍让我去广播室录音,代表全校小学生发言,批判新沙皇,然后通过广播播放。第一次上广播,既兴奋又忐忑。录音前,孙老师让我去她家,给我修改稿子,并加上了一句话:“听到新沙皇入侵珍宝岛的消息,我们中国的小学生表示极大的愤慨!”指导我朗读时注意语气的把握,要把小学生的愤慨之情表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愤慨”的词语,也让我懂得了用词的重要性。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我出外求学读高中期间,父亲也上过一回广播,是因为偷着卖了一点儿自己采的木耳,当时只允许卖给供销社,为了多卖几个钱好贴补家用,便通过邻居卖给了私人,因此被定为投机倒把,在广播里检查。我是后来听母亲说的,当时真不知道大字不认几个又讷言的父亲该有多为难。
我的少年时代,已经有很多家庭陆续置办“四大件儿”了,“四大件儿”包括收音机、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但买“四大件儿”挺难,货源不足,只能凭票供应,要提前登记、预约。票是限量的,要排队领,先来后到,发完为止。票特别少时,就采用抓阄儿的办法,很多人家为了抢到抓阄的最佳位置,头一天夜里就去商店门前排队。抓阄儿时往往全家出动,搞得人仰马翻,弄坏胳膊腿儿的事也偶有发生。这情景,在我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是计划经济时期常见的一幕。
我家买收音机时,是1970年代初期,那一次,林区商店总共进货4台,其中我家买到1台,好像是等待很久才得到购买收音机的票,忘记是不是抓阄抢到的票。因为这4台都早已有主儿,购买时就不用抢了,但这四户人家几乎都是全家出动,另外四家有同学照敏家,另外两台依稀记得有茂森和在全大哥家。把收音机从商店搬回来,当时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儿。收音机是挺大的那种,木壳的,上海产,工农兵牌。
把收音机搬进家,全家人的脸上都写满喜悦,那氛围像过节一样。由于林区远离城市,接收的信号不好,噪音大,要用天线。父亲从山上扛回一根又高又直的落叶松松木杆儿,立在房前当天线杆儿,要对准黑河城里的方向。接上从窗缝拉进来的天线,再打开收音机,噪音小多了,中短两个波段都收到了好多台,有中央台、黑龙江台,还有辽宁台、吉林台。有时也能收到更远一些的外省台,不可思议的是,两个远离林区的大草原的台,声音非常清晰,没有杂音,不知何故。这两个台,一个是当时隶属黑龙江省的呼伦贝尔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是当时隶属吉林省的哲里木人民广播电台。被称为“敌台”的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红旗广播电台,信号特别强,声音也特别清晰,一点杂音也没有。后来我到广电系统工作,听说我们是对其进行信号干扰的,但干扰过,信号也没有受到影响,也许是干扰半径还不能覆盖到100公里以外的地域?说句实在话,我还是在苏联台里第一次听到那时对我还都是陌生的作家名字,因为我上小学不久,他们就被打倒了,作品也都被禁,无从看到他们的作品,也就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当时听到的名字有巴金、老舍、曹禺、田汉、夏衍、赵树理、田间等大作家、大诗人,才知道中国不是只有几个作家、诗人。
光靠干扰还不够,当时为了搞好对苏广播,在边境城市也应该办好广播电台,比如像呼伦贝尔、哲里木人民广播电台那样信号强大的广播电台,开设中文广播和俄语广播。高满堂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爱情的边疆》,讲述的是1950年代,殷桃饰演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女大学生文艺秋,与王雷饰演的同学万声、李乃文饰演的同事宋绍山、苏联播音员维卡等人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电视剧写到了黑河人民广播电台,是殷桃饰演的主人公文艺秋的工作单位。文艺秋与一位来华留学的苏联播音员维卡在京谈跨国恋,由于中苏交恶两人天各一方,为了能与恋人在电波中重逢,文艺秋要求分配到边境城市黑河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当然电视剧是虚构的,黑河人民广播电台到1970年代才办起来,只有一个频率,没有外语广播,至今规模也不大。
二
还是回到我家新买的收音机,收音机当时绝对是奢侈品,它被摆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母亲专门找块红绒布苫在收音机上。后来大妹妹长大学会钩东西,还钩了一个帘儿苫上。
每天都听收音机,可让人陶醉、给人们带来欢笑、叫人长知识的节目,却少得可怜。那时的广播节目,单调、缺乏趣味性、种类和数量少,一个节目反反复复播放。新闻节目听的最多,当时新闻栏目少,中央台新闻栏目主要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此外,也播出广播通讯、录音特写等。1970年代初期,听到的新闻节目印象最深刻的是广播通讯,其中《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人物事迹让人感动,播音员的声音也极具感染力。还听过一个录音特写,名字记不得了,表现的是几位在云南上山下乡知青,劳动时在大森林里迷路,有关方面派出人马全力寻找,历时很多天,终于把迷路者找回的感人故事。
文艺节目听的最多的是样板戏,各台、各时段,只要打开收音机,肯定能听到样板戏,以至于《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戏,我差不多可以把整部戏的唱段、念白都背下来。粉碎“四人帮”后,杨振华、金炳昶说过一段当时很火的相声,讽刺了这一现象:调一下台,是样板戏,再调一个台,是样板戏,再调一个台,还是样板戏。杨振华模仿调台时出现的噪音,可以说惟妙惟肖。1969年夏天,也就是录制谴责苏军入侵珍宝岛的大批判稿不久,母亲带我们兄妹四人回山东老家探亲。老家的村里家家都有广播喇叭,每天早晨都被方海珍教育小强的唱段吵醒,整整3个月,竟没换过别的戏,天天都是《海港》。
有时收音机里也播一些独唱、二重唱、合唱、表演唱等歌曲,其他艺术形式几乎没有。1970年代初期,广播里陆续有了一些曲艺节目,有马季、唐杰忠、郝爱民、李文华、常宝霆、王佩元的相声。说到相声,还对广播里播出的相声进行模仿,学着写相声、说相声。1976年高中毕业回到大森林里工作,当年的秋天第一次参加护林防火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长是上海知青张捷,他让我编写表现护林防火的节目。当时广播里正播出常宝霆、王佩元的相声《挖宝》,由于反复播出,我把脚本记录下来,仿照写了相声《木头的故事》,由我和张捷合说,到护林防火联防区演出,颇受欢迎。也模仿用“贯口活儿”讲木头全身上下都是宝,提醒人们要爱护森林,珍惜树木。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贯口活儿”,是几年后到爱辉县文化馆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听了地区艺术馆创作干部王国臣老师辅导,才知晓“贯口活儿”“抖包袱”等术语。
马季、唐杰忠的《友谊颂》,表现中国建设者援外修筑坦赞铁路时与当地人民结下友谊的故事,经常播放,差不多可以背下来。还有他们二位说的《高原彩虹》《海燕》,也耳熟能详。郝爱民、李文华说的一段相声,名字想不起来了,但记得最后几句:“二嫂子,你走了吗?”“我走了!”“xxx,你睡着了吗?”“我睡着了!”“走了你怎么还在这儿?”“睡着了你怎么还说话?”
听到的曲艺节目还有刘司昌、赵连甲的山东快书,如刘司昌说的《扎义打虎》;李润杰、梁厚民的快板书,如李润杰的《劫刑车》《峻岭青松》,听的最多的是梁厚民说的《奇袭白虎团》《犟姑娘》,经常听,也能背下来;关学曾、董湘昆、马增蕙的京东大鼓、京韵大鼓、北京琴书、单弦等,如《送女上大学》。还有一个单弦联唱《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是歌颂王国福事迹的,记得第一句:王国福,家住在大白楼……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主人公高大泉,就是以王国福为原型塑造的,当然,这是很久以后才知晓的。还听过田连元说的评书小段,名字记不得了,讲的是抢救被毒蛇咬伤的朝鲜族孩子的故事,记得评书的最后一句是:“汽车,在革命的大道上前进!”听刘兰芳、袁阔成、单田芳播讲评书,是听过田连元说这个评书小段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播放的地方戏,二人转最多,东北的几个台,每天总会有一个台播放,特别是吉林和辽宁人民广播台播放的最多,二人转在那两个省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当时历史题材都不可以唱,内容多是反映新人新事的,有坐唱二人转《处处有亲人》,一位大妈来部队看儿子,却忘记是哪个“浩特”了,因为“内蒙的浩特多”,虽然走错了地方,却得到车站工作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还给接到家里,怕老人家寂寞,这家的孩子“晚上陪奶奶看电影,白天陪奶奶听广播”,直到联系上她儿子的部队为止。二人转《女队长》,我还清楚地记得里面的一段唱词并且会唱,“打猎人不怕豺狼叫,打鱼人不怕海浪翻……”。经常播放的二人转还有《小鹰展翅》,当时也播放过单出头,名字叫什么忘记了。《处处有亲人》《小鹰展翅》是吉林排演的,《女队长》是辽宁排演的。还有一个节目是常德丝弦《社会主义新事多》,经常播放,还记得第一句,“红太阳光辉照山河,社会主义新事多,伊儿呦伊儿呦……”,旋律好听,以后再也没有听过这种曲艺节目形式。当时还有一个河南坠子也经常播放,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十个大鸡子”一句,大概是讲拥军的故事。播出的评剧,好像只有一出《向阳商店》。就这些节目,翻来覆去地放,听的日久天长,就差不多都会模仿着唱或说了。
三
1970年代初期,大约是1973年前后,听到了俞逊发等演奏家的笛子独奏曲,如《牧民新歌》《扬鞭催马运粮忙》;闵惠芬、王国潼的二胡独奏曲,如《赛马》《江河水》。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良宵》,是粉碎“四人帮”后听到的。听到的还有刘德海的琵琶独奏曲《十面埋伏》,刘明源的板胡独奏曲,刘占宽的唢呐独奏曲,还有古筝独奏曲《战台风》、小提琴独奏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等。由于身边有上海知青的缘故,喜欢听用江南方言演唱的《社员挑河泥》,表现的是与北疆迥异的地域风情和演唱风格。有时也能听到上海知青张捷、张时云等人唱,也学着模仿哼唱:“撒啦啦子呦,社员挑河泥,心里真欢喜……”广东音乐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听到的,如《雨打芭蕉》《旱天雷》《步步高》等,旋律优美,很喜欢听。
那时通过听广播和看电影,熟悉名字的歌唱家有:郭兰英、朱逢博、叶佩英、马玉涛、马国光、吕文科、胡松华、孙家馨、贾世俊、刘秉义、邓玉华、才旦卓玛、张映哲、张越男、贠恩凤、何纪光、郭颂、李世荣、韦有琴、黄仁顺、郭芙美、张振富、耿莲凤、马玉梅、李秀文、陆青霜、边桂荣、董振厚、娜仁花、高娃、郑湘娟、李双江、吴雁泽、卞小贞、李谷一、庄如珍、邱子敏、刘桂琴、蒋大为等,有些歌唱演员的名字当时是耳熟能详的,也有的是近年刷微信才知晓当时听到的歌曲演唱者的名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听到演唱比较多的歌唱家,除了前面提到的郭兰英、朱逢博、李谷一、李双江、蒋大为、李秀文、卞小贞等人外,还有王昆、寇家伦、李光曦、孟贵彬、姜嘉锵、付培蒂、王玉珍、王音璇、杜丽华、钱曼华、罗天婵、任桂珍、于淑珍、韩之萍、张暴默、关贵敏、殷秀梅、郑绪岚、欧阳劲松、靳玉竹、任雁、朱明瑛、远征、苏小明、成方圆、沈小岑、程琳、王洁实、谢莉斯、吴国松、秦蕾、德德玛、张正宜、程桂兰、曹莉、关牧村、冯健雪、金曼、马太萱等。
1970年代初期到中期,除了在电影里听到和在收音机里听到的电影插曲外,在收音机里经常听到的创作歌曲有:《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红太阳照边疆》《大寨人心向红太阳》《我站在虎头山上》《大寨红花遍地开》《老房东查铺》《北京颂歌》《回延安》《延安颂》《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挑担茶叶上北京》《我心中的金凤凰》《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海上南泥湾》《南渡江》《伐木工人之歌》《咱是生产队的半边天》《我为革命下厨房》《我送报刊走的忙》《真像一对亲兄弟》《天安门前留个影》《阿瓦人民唱新歌》《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为伟大的祖国站岗》《战斗进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远航》《解放军野营到山村》《师长有床绿军被》《脱下军装不下岗》《军营套曲(包括投弹歌、夜行军歌、敌人怕啥咱就练啥等六首)》《爱舰爱岛爱海洋》《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银球飞舞花盛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听过的少儿歌曲有《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友谊开花万里香》《火车向着韶山跑》《小司机》《骑上小木马》《小松树》《喂鸡》《井冈山下种南瓜》《革命故事会》《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等。把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称为“孔老二”,显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奠基者之一的孔圣人的不尊重和蔑视,这是当时开展的运动使然,我们当时也盲目跟着批、跟着唱。听的最多的是带有那个时代特征的歌曲,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学大寨赶大寨》等,前者近乎绑架式宣传,反反复复唱“就是好”,不容许有任何质疑,中间还穿插呐喊,看来没有更好的词可以替代了,就像一首“语录歌”,整首歌只有五个字,“要斗私批修”,就翻来覆去地唱,中间也穿插一句呐喊。
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复排了《长征组歌》,在广播里播放,听到了当时已经熟悉名字也有不熟悉名字的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王克正、杨亦然、耿莲凤、王伯华等人的独唱、领唱、二重唱,对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出的合唱印象最深。我所在的林业中学,吴守垣、杨小慧、吴绍春老师带我们排演了《长征组歌》中的七个部分:《告别》《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报喜》和《大会师》。老师从八里桥部队借来了军装当我们的演出服,在爱辉县林业系统和八里桥、三站的驻军部队演出了一大圈儿,也产生一定影响。高中毕业前,请师生留言,校长的留言是:你在文艺宣传方面很有才能,希望你毕业后发挥这个优势,为三大革命做出贡献。没想到由于参加演出,让校长注意到,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艺考,不然也报考艺术类院校试一试。其实校长高估了我,艺术方面还谈不上天赋过人,尤其唱歌更难登大雅之堂,如果报考话剧表演或编剧专业,或许有一线希望,这和我曾在小学和高中时主演过话剧有一些关系。
那段时间,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率先复出了,我们听到了《黄河大合唱》这部艺术精品,在当时可以说是空谷足音。近来从媒体上看到当事人的回忆,原来是冼星海的女儿给毛泽东写了信,才有了聂耳和冼星海的作品演出和广播播放。1975年,是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中央乐团复排了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全曲,以为纪念。指挥是严良堃,演唱者是郭淑珍、黎信昌等,朗诵者是王冰。赶上暑假还是寒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出,其中的大多数歌曲如《黄河颂》《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等,就是这样听会的。由于多次反复播放,我边听边记,把朗诵词记了下来,有同学还借去传抄30多年过去了,自己也常常模仿着朗诵,至今还对王冰的朗诵记忆犹新。还有聂耳、冼星海创作的《卖报歌》《新的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毕业歌》《只怕不抵抗》《到敌人后方去》《二月里来》《金蛇狂舞》等歌曲和乐曲,也是这个时期听到的。在这期间,还推出了《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区干部是好作风》等江西民歌五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翻身道情》《军民大生产》等陕北民歌。还有大革命时期的歌曲和抗战歌曲,如《工农革命歌》《工农齐武装》《抗日之歌》《大刀进行曲》《前进歌》等。上面这些歌曲都是在收音机里听到,其中大部分也是这样听会的。当时比较喜欢唱《卖报歌》《毕业歌》《二月里来》等,江西民歌和陕北民歌也经常听和唱。近年,我到沪上的一所民办大学工作,参加学校组织的毕业典礼,唱聂耳的《毕业歌》是一项重要程序,可见这首歌的恒久魅力。
四
电影录音剪辑也是那时广播电台的主要节目,都配有解说。由于林区个把月才来一次电影队,看到的电影有限,好多电影都是听来的。比如国产电影《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春苗》《征途》等;国外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沸腾的生活》《橡树,十万火急》《追捕》《望乡》等,也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
特殊历史时期听到的文学节目不多,记忆深刻的有贺敬之的诗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高红十等作者的长诗《理想之歌》,浩然的长篇小说《西沙儿女》,张永枚的长篇诗报告《西沙之战》,王书怀的长诗《张勇之歌》等。
还有广播剧,也是那时的主打节目,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由黑龙江广播电视艺术团制作的广播剧,水准很高,在全国的省级电台中,都名列前茅,其中广播剧编剧、导演有高广义、郭银龙、王波等,到后来还有王锐、饶津发、矫崇兴,我认识的王国臣老师等,演员有郑淑琴、曹阵、王淑萍、李慧敏、杜玉泉、萧淑芳、姜萍等,有的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演员。其中听到郭银龙、王波、郑淑琴、曹阵编导、主演的广播剧最多,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郑淑琴、曹阵的声音也铭刻在心。
那个年代,颇能吸引人的节目是小说连续广播,也记住了省台和中央台几位播讲小说的名字。先说省电台,男声播讲属曹阵(当时以为也可能是“振”“镇”“震”)最好。每天播完,播音员说:“是由曹阵播讲的,”邻居孙婶以为他叫“曹阵波”,说曹阵波讲的很好云云,这让我们乐了很久。他播讲最为精彩的一部小说是《桐柏英雄》,在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氛围里,这部小说的故事可以说跌宕起伏,情节可以说扣人心弦,无论男女老少,到点儿就齐聚收音机前或大喇叭下,听赵小花的曲折故事。赵小花是那个时代不多见的一个亮点,尤其是激动了我们少年的心。他还播讲了《渔岛怒潮》,战争和反特故事,永远吸引男孩子。当时听过曹阵播讲的小说还有本省作家林予、谢树创作的《咆哮的松花江》,里面有许多黑龙江乡土化语言。本土作家写本土生活的作品听来亲切,留下的印象也深刻,除了《咆哮的松花江》,还有工人出身的本土作家郭先红的长篇小说《征途》,是以黑河地区逊克县上山下乡知青金训华烈士的事迹创作的。另外还有本土诗人王书坏的叙事长诗《张勇之歌》,是女声播讲,播讲人是陈阿喜,她的声音甜美、动听,极富感染力,让我难以忘怀。《张勇之歌》是她和曹阵联合演播的,我听过不止一次,印象深刻。她播讲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中篇小说《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等,都脍炙人口。后来她调到北京,在中央广播文工团任演员,在中央台继续播讲小说。粉碎“四人帮”后,听过她播讲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等,还听过她朗读的许多文学作品。
中央台曹灿播讲的《矿山风云》《向阳院的故事》《闪闪的红星》《高玉宝》《新来的小石柱》《战地红缨》等表现儿童故事或少年英雄故事的小说,也让我铭刻在心,因为他的嗓音挺特别。还听过他播讲的《艳阳天》《李自成》等。
粉碎“四人帮”后,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播讲的小说,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也有了新的播讲者。陆续听到了曾被打入冷宫的长篇小说播讲,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等。也听过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如冯苓植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等。
1978年或1979年,听过金乃千播讲的《东方》,这是当代作家魏巍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当时听的如醉如痴,因为小说不单单写战争,还写了爱情,写了人性。记得小说里,志愿军军官里还有反面人物形象,这在当时是觉得很独特的。小说里的郭祥、杨雪等正面人物形象,以及陆希荣的反面人物形象,都让人印象深刻;情节扣人心弦,抓人耳根。还听过张家声、牟云、瞿弦和、张筠英等艺术家播讲的小说。
恢复高考后,考入师范学校读中文专业,我带了一个小收音机去。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倒是不经常听,因为播讲时间刚好与上晚自习时间冲突。记得班级的几位女同学,喜欢听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播讲时,就跑到教室外的双杠前,聚在一起收听,沉醉其间。
在矿山工作时,一次去北戴河学习,同行的省煤田地质公司的单国俊带了一个小半导体。开班那天中午,我们从海边游泳回来,准备睡午觉,但单国俊正在收听小说连续广播节目,当时播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天正好讲到主人公孙少平的爱情故事,不知不觉间,室内七八个人全都竖起了耳朵,单国俊也适时调大了音量。那天的午觉谁也没睡成,以后的几天中午也依然如故。小说先在中央台播出,然后才正式出版,播出和出版后,好评如潮,成为一部难得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上乘长篇,当然,这都是很久以后才知晓的。小说人物形象鲜明,故事精彩,播讲的也特精彩,但播讲者是当时听了比较陌生的名字:李野墨。这段听广播的经历发生时,已是1980年代中后期。
五
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特别悲伤的消息是周恩来总理逝世,那时我正在爱辉县林业中学读9年级,住宿条件有限,我们班级所有男生都挤在一个大寝室里住。当时同学还没有一个人有收音机,周总理去世后,为了及时收听新闻,一位同学把吴守垣老师的收音机借来了,这样每天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他只好也跑到我们宿舍来听。学校自发地搞了悼念活动,还在教室设置了灵堂,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组织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不知道老师在哪里找到了哀乐的唱片,也记不得在哪里找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后来听说中央下发了通知,各地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不许设灵堂,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也许是山高皇帝远,我们学校没有接到通知?或者校领导没有执行通知?不管怎么说,校领导和老师的举动,让我们充分表达了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之情。我们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佩白花、戴黑纱。记得一天早晨,大吴老师又来收听,当收音机里播音员说:把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大吴老师激动地、也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浙南口音喊了一句:“好啊!”他的神态如在眼前。
再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是在同一年,这时我已高中毕业回林区上班。一天我坐敞车由林区小镇去黑河治牙,途经一个叫西山后的村子,车停下来休息,司机与这里许多人都熟,我们听到大队的大喇叭正播放很低沉的乐曲(后来知道那叫哀乐)。一位司机熟识的人过来,趴在车厢板上用悲伤的、很小的声音说:“主席去世了。”过一会儿,大喇叭里开始播《告全国各族人民书》。觉得难以置信,当时有天塌地陷之感,被巨大的悲伤和绝望袭击着。到了黑河,在县林业招待所住下后,我就随着自发的人流到三百旁的劳保商店领免费发放的黑纱,然后戴上。记不清是一直住在招待所还是再一次来城里,9月18日,我又去参加了在黑河人民广场举办的追悼会,先是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广播实况,然后黑河地区再开追悼会。那天,黑河城里几乎所有人都齐聚广场,广场四周还架起了高射炮,估计当时军方进入了一级战备,因黑河地处边境,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担心对岸会趁机入侵,等待开会的时间,不知是谁发现了高空有一黑点,于是坐在广场上的几万人全都仰头看,以为是对岸派来轰炸的飞机,气氛很紧张。当时广场旁还有救护车,还真有人让救护车拉走,不知道是悲痛欲绝而晕倒,还是中暑晕倒,那天天气晴好,温度也颇高。
六
真正受益于广播是在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高中毕业回大森林里工作,上班几个月后广播里传来“大快人心事”。这年冬天第一次去山场伐木,离家有四五十里路,我们住在帐篷里。不知是谁带了收音机,每晚的精彩节目陪伴我们度过了漫长的冬夜。也奇怪,在林区小镇接收广播信号需要立杆子,在山场,距离城市更远了,信号却更好,声音也更清晰,不用外接天线,也许我们采伐点的帐篷,是架在山山坳里,海拔更高一些的缘故?那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兴奋点,那些我偷着学会哼唱的一首首老歌儿陆续解禁。比我们大几岁的上海知青张捷、贺永国、谈官宝等人,老歌儿都会唱,收音机里唱,他们也跟着唱,如播《刘三姐》时,张捷等人几乎全都能跟着唱出来。王昆的《抗日将士出征歌》《夫妻识字》、郭兰英(她复出较早一些)的《绣金匾》《八月十五月儿明》、邓玉华的《革命熔炉火最红》、王玉珍的《洪湖水,浪打浪》、任桂珍的《绣红旗》、黄婉秋的《刘三姐》、胡松华和杜丽华的《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等老歌儿,都是在帐篷里跟收音机学唱的。还跟收音机学唱了一些新歌,如李光曦的《祝酒歌》、韩芝萍的《歌唱敬爱的周总理》等。
每一个被打入冷宫的艺术家的名字出现,我们就欢呼一阵,声音传出帐篷,在山谷里回荡。儿少时听惯了许多歌曲的激昂、铿锵,冷不丁听这些婉转、抒情的歌曲,真有如品尝了美味佳肴、玉液琼浆一般,那感受跟从前就是不一样。我们上高中时,家在城里的慕华同学放假回城学了几首老歌儿,还有几位班上同学跟四中到二站公社搞开门办学的同学,学了几首港台歌曲,他们经常偷偷唱,被当作唱黄色歌曲,受到批判。记得歌中有歌词“阿哥阿妹情意长”“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再来一杯苦的咖啡”等歌曲,还有一首歌词是:“再见吧,春光明媚的巴厘海湾,我将到遥远的地方……青春是无限美好!”。以后才知道第一个是歌曲《婚誓》的第一句,是电影《芦笙恋歌》插曲;第二个是王洛宾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第三个是台湾歌手姚苏蓉演唱的《我与咖啡》中的一句,这是很久以后才知晓的。第四个旋律最动听,至今不知道歌名是什么。
为庆祝粉碎“四人帮”,纪念周总理,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每晚都播放诗歌朗诵音乐会。诗歌朗诵音乐会有曹灿、周正、姜湘臣、董行佶、殷之光、张家声、金乃千、瞿弦和、郑振瑶、张筠英、牟云、陈阿喜等人的诗朗诵,有歌唱家演唱歌曲。播音艺术家夏青、葛兰、林田、费寄平、铁城、方明、林如、雅坤、虹云、王欢、傅成励、丁然、黎江、于芳、马黎、潘捷等也朗诵文学作品,解说电影录音剪辑。听他们的朗诵,真是享受听觉盛宴,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朗诵艺术的魅力,就从那时起,我就喜欢上了朗诵。2010年代的一个夏天,在河南大学参加新闻学院成立20周年庆典晚会,现场听到虹云老师的朗诵,并在同住的酒店大堂见了一面并聊了几句,这是后话。殷之光朗诵的《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打动我的心,感受到了周总理为党的事业日理万机的辛劳;董行佶朗诵郭小川的《昆仑山的演说》,使我觉得就如同有一位伟人正站在昆仑山顶,指点江山。听到朗诵郭小川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更让我体会到诗歌的无穷魅力。
相声是当时各家广播电台喜欢播出的节目样式,1976年10月以后,听到最多的是侯宝林与郭全保、侯宝林与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如《夜行记》《醉酒》《戏剧与方言》《说方言》《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改行》等。还有刘宝瑞、郝爱民合说的相声《宁波话》,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黄半仙》,马季说的单口相声《打电话》,杨振华与金炳昶合说的《下象棋》《好梦不长》,苏文茂、王佩元合说的《批三国》,苏文茂说的单口相声《扔靴子》,高英培与范振钰合说的《钓鱼》,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等,都可以说百听不厌。
京剧、评剧、昆曲、豫剧、越剧、黄梅戏等都经常播出全剧或选段,中央台、黑龙江台也开办了京剧或戏曲栏目,记得黑龙江台开设了《老张聊戏》栏目,我这个时候从收音机里知道了许多戏剧大师和艺术家的名字,如京剧的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李多奎、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谭富英、裘盛戎、奚啸伯、李少春、张君秋、李和曾、赵燕侠、关肃霜、刘秀荣、杨秋玲等。还有评剧的新凤霞、小白玉霜,越剧的袁雪芬、傅全香、吕瑞英、范瑞娟、徐玉兰、王文娟,黄梅戏的严凤英,粤剧的红线女,吕剧的郎咸芬等。
也听了很多话剧,最早在广播里听到的话剧,大约是我家买收音机后不久,是关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题材,名字不记得了。当时对话剧的印象并不好,觉得有点儿吵,听不清台词。真正感受话剧的魅力是新时期以后,陆续听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报春花》《姜花开了的时候》《双人浪漫曲》等。特别是听到北京人艺的《屈原》《蔡文姬》《雷雨》《龙须沟》《伊索》《丹心谱》等,才感到话剧艺术的神奇,原来语言能如此让人震撼。知道了老舍、曹禺、焦菊隐、郑榕、刁光覃、朱琳、蓝天野、董行佶、于是之、童超、苏民、英若诚等一批国宝级剧作家、导演、表演艺术家的名字,被表演艺术家的声音所迷恋。
七
渐渐地电台节目丰富了,样板戏播的少了,“文革”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栏目又恢复播出了,如《小喇叭》节目,《星星火炬》节目。这时我知道了孙敬修爷爷,喜欢听他讲故事。后来有了适合我这个年龄段听的《青春年华》节目,主播张悦的嗓音异常甜美,一次她回答听众的提问解释她的名字:想给听众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欣喜。还有一次在节目里,她讲起了自己,她是从内蒙古草原,考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由于赶上“文革”,当时只有初中学历。她边做好播音工作,边坚持学习,终于获得自学考试文凭。当时听了她的故事,觉得很励志,也感到很亲切。也很喜欢听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多年以后,从黑河籍剧作家、散文家刘邦厚老师的散文里,才知道徐曼是黑河人,小时候就在黑河西郊的振边酒厂里长大。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阅读与欣赏》和《文学之窗》节目,它们使我受益匪浅。由于我上学期间特别是高中的两年几乎没有学到多少功课,加上在大森林里也找不到书读,我能获得一些文学知识,很大一部分来自广播。没有收音机,后来恢复高考时,我想考上学几乎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能考取师范,主要是靠语文成绩。入学后,班主任赵宗乙老师告诉我,我的语文成绩是全班最高的,作文满分。得以录取,除了感谢从小学一年级到九年级教过我的老师、感谢父母外,也要感谢收音机,广播里的节目拓宽了我的视野。张家声、曹灿、牟云、张筠英、陈阿喜、郑振谣等人的朗诵,如打开了一扇窗,使我认识了文学王国的美丽、神奇。听他们朗诵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秦牧的《土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贾平凹的《满月儿》等,有身临其境之感,文中的主人公如在目前。
我能报上名参加高考,也得益于广播。是1970年代的最后一年的高考,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高考通知是由县林业科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基层单位,由于上海知青等已大都返城,一位主管领导想当然地以为林区子弟没有人报名参加高考,这个通知既没有在全场大会上宣读,也没有在大喇叭里通知。我当时正天天等着报考通知,眼看时间临近,还没有音讯。忽一日,听省台新闻播出:今年的高考报名工作到今天结束,全省有多少多少人报名……我一听傻眼了,赶紧去找场领导,主管的这位领导答复说:“通知早就来了,我以为上海知青、黑河知青都走了,本地知青就没有人报名参加高考了,就没有发。”这个回答让我无语,也不知从哪里来一股急劲,当天就请假坐带“炮车”(即带拖斗、无大箱板儿的货车,可以装十多米长的木头)的拉大木头汽车下山了,坐在十多米长的原木上面,这样乘车是很危险的,时间紧迫,也顾不了那么多,再说林区小镇通黑河的客车一周只有一次,没法等,就急三火四赶到近150公里外的黑河。爱辉县林业科主管教育的李桂芬老师善解人意,她听说了情况,二话不说,冒雨陪我去县教育科,主管招生的两位张老师也很热心,他们从留出的机动名额中给我报了名,我还替我妹妹及另外两人报上了名。结果那年我成为“大学漏子”,被录取到地区师范学校。如果不是听广播,我也许就错过了那一年高考的机会,那我的人生也就会重新改写。
入学后,有一个小收音机带在身边,记不清是父母给我买的,还是我自己买的。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最后评出15首,和同宿舍的志照、德功、贺伟、郭军、光明等同学还认真参加投票,结果出来,我们投票的大部分歌曲入选,活动结束,还收到中央台给我们每个参加投票同学寄来的入选歌曲的歌片儿(折叠式的),入选歌曲都是我们喜欢听、喜欢唱的,有《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青春啊青春》《永远和你在一道》《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远方的书信乘风来》等。《歌曲》月刊举办的1980年歌曲评奖,我们也参加了,也收到了歌片儿。获奖歌曲有我们当时喜欢的《军港之夜》《美丽的心灵》《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红杉树》《我爱家乡的山和水》《太湖美》《浪花啊浪花》《清晨,我们踏上小道》《驼铃》《思亲曲》《戒烟歌》《心中的玫瑰》《啊,故乡》《彩云归》《生活是这样美好》《妈妈,看看我吧》《青春多美好》。这些歌曲都是经常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也是边听边跟着学会唱的。
我曾跟收音机听广播电视英语讲座,学习英语,是陈琳主编的教材,只是后来毕业再次上班没有坚持下来。
在师范的第二年,就有电视看了,这是个传媒事业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也预示着广播开始走上艰难之路。听广播很快就让位给看电视了,自此,我们与广播渐行渐远。在师范上学时,还不能直接看到中央电视台、省电视台的节目,看到的是黑河地区广播电视局播放的录像。我们自己还没有开始拍电视连续剧,看的都是国外的电影、电视剧,记得看过《复活》《红与黑》等。录音机的出现也给广播带来一定冲击,也是在师范的第二年,盒式录音机悄然出现,很快同宿舍的郭军同学家里买了一台,他带到学校,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有了电视看、录音机听,就如有了新朋友,但忘记广播这个老朋友是不应该的,广播这位老朋友对于我而言,是恩重如山的。我与广播情缘颇深,后来竟然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从事管理工作十年整,再后来又转行到内地高校,从事广播电视专业的教学工作。这是我在大森林里听广播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的。
广播,几乎陪伴我度过整个1970年代,她伴随和见证了我的青葱岁月,伴随和见证了我的成长。她如同一个魔盒,给我展现玄妙神奇,让理想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她如同一座看不见的舞台,让我如置身台下,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人间的悲欢离合;她如同一位老师,传道受业解惑,循循善诱,令我获益匪浅。
那逝去了的如歌岁月,那飘远了的如烟往事,那依稀回荡在耳畔的声音……
(刊发于《太湖》杂志2025年第2期)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