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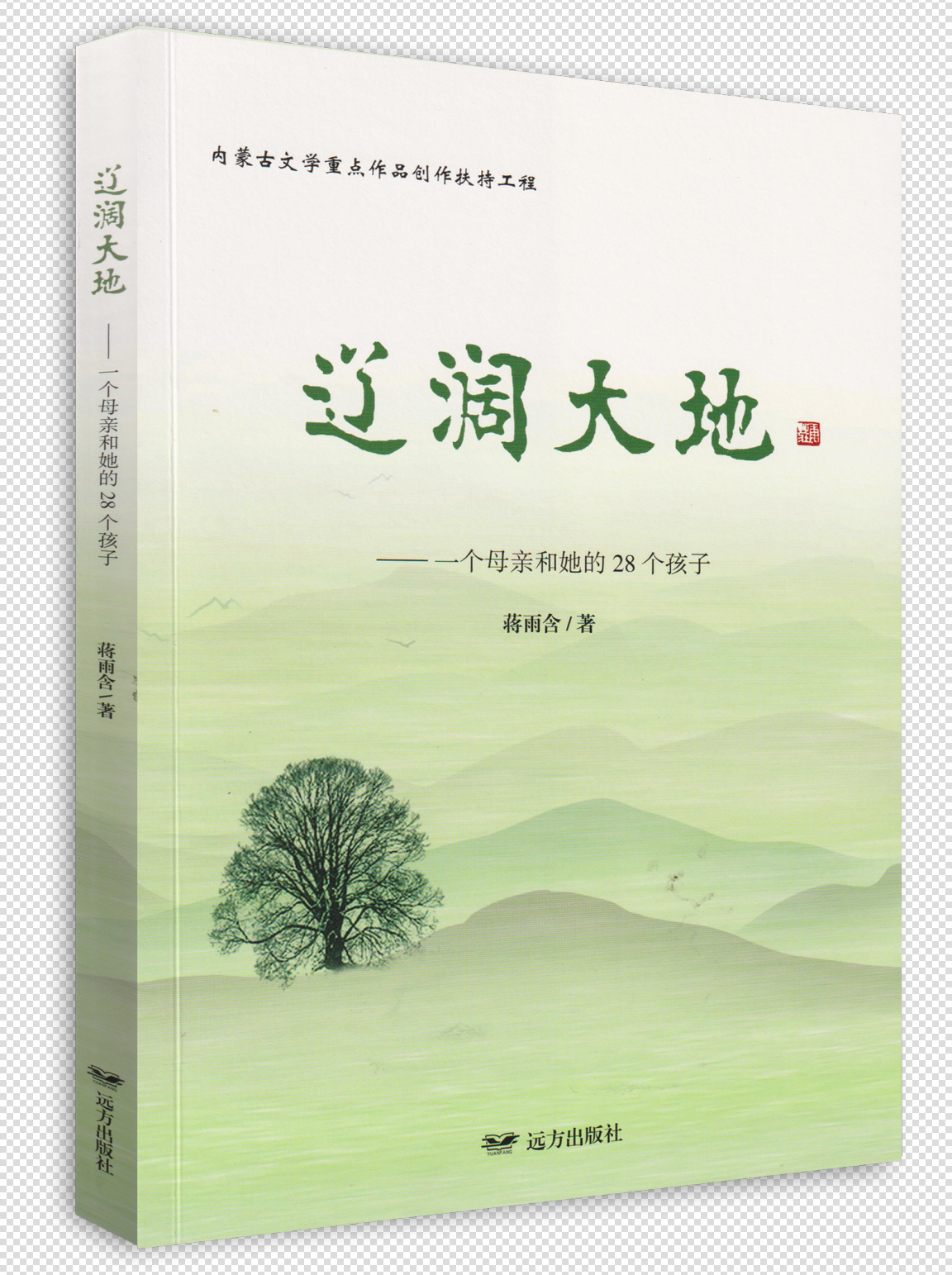
此心安处
——读蒋雨含《辽阔大地》
作者:逃之夭夭
一直喜欢雨含老师的诗,细腻精致,唯美隽永,最近读了雨含老师关于都贵玛老人的传记文学《辽阔大地》,读到的又是雨含老师的另一种风格:尽量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去书写一位朴实无华的人物,唯一不变的,依然是细腻的情感倾诉,带着大草原青草露珠的芬芳。
《辽阔大地》的叙事是多线性的,情感表达也有多个维度,限于能力,我无法面面俱到的去解读,只能牵住一个线头拉长扩展,更多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吧。《辽阔大地》中有一段关于上海孤儿参加寻亲大会的描述“在寻亲大会上,你最不难看到的就是焦虑、凄惶、悲伤这样的表情,但是你在内蒙古寻亲团的人中看不到,他们好像不是来寻亲的,只是来看寻亲的,既身在其中,又置身其外。一说寻亲,找丢失多年的亲人,就会觉得这些失去亲人的人可怜,但是这些‘国家的孩子’身上表露的很少,他们的生活虽然不是特别富有,但是他们大多数都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满意,一看就是在有爱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们仿若原生家庭一样地长大,享受着父母之爱,享受着家庭温暖,他们身上自尊、自爱、守礼、内敛的那股劲儿,特别难得。”
读到此处,忍不住触发思考,大家都知道,乡愁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得像酒一样的情怀,湖南凤凰沈从文墓地附近有一块黄石碑,是由黄永玉题写的“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家乡。”体现出沈从文对凤凰家乡的依恋与热爱,古今各种诗词歌赋里关于乡愁的描写多到不可胜数,可为什么在这些从草原来到故乡的孤儿身上却没有太多这样的对故乡的依恋呢?
我觉得答案就是蒋老师这本书的名字——“辽阔大地”,因为草原足够大,它的大不仅是地域上的广袤无垠,更有草原人民胸襟的博大包容。正如黑梅老师在分享会发言中提到的“关于《辽阔草原》,我和你们理解不一样,你们了解的“辽阔”是草原,我了解的“辽阔”是母亲。”习惯了在草原上策马驰骋的孩子们离不开杜尔伯特草原,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乡。
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甚至身份,但同时,内心强大的人也可以把陌生的环境变成自己的家乡,苏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到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把每一个呆过的地方(包括一些“荒蛮之地”)很快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设,“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最好的写照。
上周耀东兄去额济纳旗上班,我顺路办事结伴而行,谈饮之间耀东兄也有些许无奈“一跟人说起来我从呼和浩特调到阿拉善了,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点头赞许,嗯,对的对的,阿拉善的工资高”,“他妈的就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的情怀吗?”诚哉斯言,耀东兄到任后,立即着手编撰《阿拉善盟税史·额济纳卷》,但面临的问题是可供参考的数据极度匮乏,为了查找资料,他往返奔波于额济纳、呼和浩特、阿左旗之间,最近的距离也超过六百公里,且交通极不便利,结果单位里还有人反映他不认真上班。从左旗去额济纳路上,耀东兄一路指点何处是汉李陵与匈奴古战场,谈起李陵苏武往事,诸多误会,不胜感慨。目前,五万字的《额济纳卷》即将脱稿,遥祝耀东兄情怀依旧。
有刘不伟氏,立志文学,北漂多年,可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中年为了照顾女儿,离京北上,寓居青城,贫居陋巷,一箪食,一壶浆,终不改其志。又性喜奖掖后进,以扶持青年诗人为任,孜孜不倦,乐在其中,以苍颜白发每天酒醉颓然于少男少女之间,笑得像佛一样,有大自在。
更有内蒙古文学杂志社阿霞等诸位老师,深耕厚植于内蒙古这块文学荒瘠之地,默默坚守,红尘万丈,只取一瓢,把一片文学库布其沙漠变成了绿洲。《草原》杂志,捧一泓清泉,掬一缕芬芳,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此致以诚挚敬意。
“此心安处是吾乡”,借苏子此言与诸君共勉。
2023.11.26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