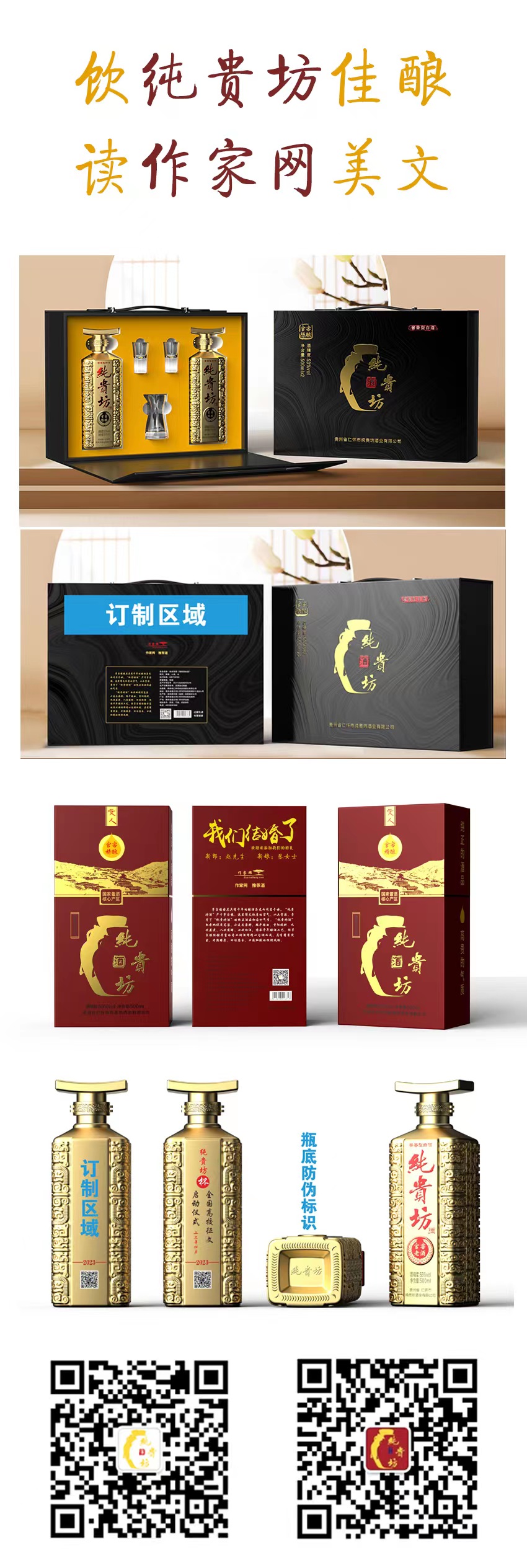木槿花开
木槿花开
作者:王军
当门前暖暖的阳光被暮春的风吹在树梢上时,突然我想起了屋后小道旁那几棵木槿树。于是,便从家里欣喜地跑了过去,瞅着风中微微摇摆的树叶,心里有些纳闷,也不停地思忖着,原来这就是多年疑惑的木槿树,还开着淡紫色像喇叭形状的花。
木槿在我老家叫“木佳叶”,祖祖辈辈这么叫,字典中都难查找。儿时,因受父辈的影响,每每见到它也常跟着长辈们一样念着。久而久之,这一念便深深地烙进了心里,没再从心中对它的学名加以纠正。在往后的生活中,总误以为北方的木槿与儿时所见的树木不一样,不属同一个物种。每当这时,心里也就凭空臆断它不是家乡的木佳叶,甚至还拍着照片带回去与家乡的叶子相比较。
我的老家在大别山地区,地处亚热带气候带,那里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温暖湿润,四季分明,特别适宜木槿的习性,有时见它在沟沟坎坎边生长着,旺盛地冒出叶子,张开着粉紫的花瓣。但我们又多数只是瞟上几眼,就匆匆地离开了。
那时,在父母的心中木槿花是不能摘下来拿在手里玩的。母亲说:“那花有毒,闻着鼻子长疮。”是不是真的长疮,我们没有闻过,也在母亲的提示后不敢再碰木槿花。有时偶尔见到满树花开,粉粉的、紫紫的,在树上无忧无虑地敞开着喇叭口,很想凑近处看一看把它摘下来,但怕它的花粉钻进鼻子里,长着像母亲说的那种“杠鸡”疮。
有时想,祖辈流传的警示或告诫自然有它的道理。许是上千年或几辈人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他们一代代告诉儿女,一代代这样谆谆善诱。
事实上,木槿花没有毒情,许是父辈们将它误认作有毒的夹竹桃。然而,就是这个被人们心中视为“杂树”的木槿,在我那个贫瘠的山村那个灾荒的年代却成了“香饽饽”。
它的树枝常在开春里冒出细小的嫩叶。湾里人见后总是提着菜篓子到田边地头、河坎沟坡旁把嫩叶采摘下来,拿回家与事先磨好的米粉一起蒸着吃。
米粉是用村头的石磨磨出来的,不像白面那么细腻,抓在手里感觉有些粗糙,颗粒颗粒的。母亲把它和洗净的木槿叶掺和在一起便放进灶锅里蒸着。蒸熟的木槿叶沾上一层厚厚的米粉,每次揭起锅盖,一股清香的味儿瞬间钻进了心里。
那时,每到春天木槿树长出幼小的嫩叶我们家常去山边采回来蒸着当饭吃。母亲说:“忆苦思甜,家里没饭时就吃它。”我望着母亲,想着她的话,端着香喷喷的木槿饭,心里觉得母亲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心想那么香的木槿饭,不像是苦日子的饭菜。
没吃完的木槿饭,会被母亲小心翼翼地装进竹篓子里,高高挂在厨屋门边。我与弟弟趁她在地里干活,偷偷地搬着板凳站上去,伸手去够。母亲发现时,那竹篓子的木槿饭已所剩无几。
每次,我们望着放工回来的母亲伸手提下竹篓子时,心里怦怦乱跳,害怕母亲责备起来,说我们在偷吃。
但母亲发现后脸上却露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一次,清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见她一瘸一拐地㧟着篓子跨进门坎那一刹那间,心里一惊,便跑了过去……
母亲放下篓子满不在意地说:“不碍事,脚踩空了崴了一下。”
说完,母亲径直地去了厨屋从水缸里舀起水洗着木槿叶。那天,母亲把蒸好的木槿饭盛在竹篓里仍挂在厨屋的门旁边。那天,我们兄弟没再搬起板凳倚着门边伸手够着。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后,那竹篓子的木槿饭仍挂在那里。
随后,母亲取下它在锅里热好后盛在碗里说了一句:“守规矩,才有饱饭吃。”打此,我们兄弟没再闹着抢抓竹篓子里的木槿饭,也没再偷吃厨屋里上一顿剩下来的东西。但一次木槿花开却吸引了我,瞅着绿油油的木槿树,我叫着弟弟扛着竹杆一起去摘木槿叶。
采木槿叶时,我们怕木槿花染在身上长着一种疮,便用竹杆把树上的花全部打掉,拨弄远远的,好爬到树枝上摘着密密匝匝的叶子。
那叶子厚厚的,硬硬的,摸着有些扎手。回家后,母亲一见说了一句醍醐灌顶的话,“傻孩子,开花的木佳叶不能吃。”我们望着竹篓子的“木佳叶”,似乎明白了生活中的一些奥妙。
往后,我们没再去采摘它。偶尔在外地见着木槿树,望着那树上长着淡紫色的花朵,便想起那时喷香喷香的木槿饭。这么多年,再没能吃上一次。每次回到家乡,那田埂沟边的木槿树嫩叶依旧,却没什么人采来吃了,但那股“忆苦思甜”的味儿,如乡悉,似母爱,时时从记忆深处飘起,萦绕在心间……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