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表弟罗上林
怀念表弟罗上林
作者:杨远新
一般来讲,表兄表弟之间,从年幼到年轻阶段,相互都很亲近,甚至很密切,那是因为互为玩伴,互为依靠,彼此需要对方。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结婚成家后,各自有了新的玩伴和依靠,表兄表弟就渐渐疏淡了。这似乎是规律,也符合人之常情。但我与表弟罗上林则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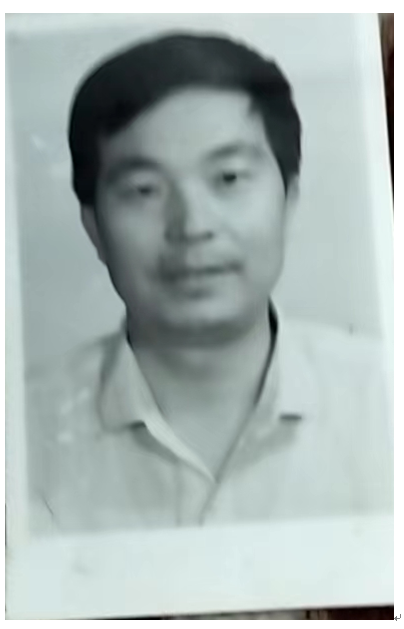
罗上林年轻时留影
这与我的母亲与他的母亲有着极大的内在关系。我母亲李清凤是姊妹中的老大,他母亲李清枝是姊妹中的老二,姐妹俩年龄悬殊不大,仅仅两岁之差。姐妹俩从小就相依为命。我母亲是柔中有刚,他母亲则是刚中有柔,往往相得益彰。
记得自我稍稍明白事理开始,就常听外祖母以骄傲的口吻说起她的两个女儿上曹家湖挖藕,为她脸上争得光彩的事。
洞庭湖区挖藕,这本是男人干的活,从古至今皆无变化。我外祖父辈、曾外祖父辈及以上,家里男丁多,都是这样传承的。可到了我母亲我大姨这一辈,家里缺少的就是男丁。这是因为我舅舅李少清,族名李承载,比我大姨晚出生十年,尚处在年幼阶段,但凡男人干的农活,我母亲我大姨都要干,挑起男人的重担,为我外祖父外祖母分忧。
那是一个无大风,有阳光的冬日,离过年只有几步远了,洞庭湖人家都在准备各种各样的过年货,其中湖藕是必不可少的,到了过年那天,将藕放进腊肉一锅炖煮,白生生的藕便变得乌油油,用筷子从中挑取一节,送到嘴边,香气扑鼻,顺势一口咬下去,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哎呀!粉坨哒!好吃得狠!”炖藕咬断处,牵出缕缕藕丝,比蚕丝还要细,还要密,长度你想拉多长都可以。炖藕切片、切丁,切丝,放上绿葱红椒和白色的姜丝烩炒,是除夕那天的团年饭,和进入正月里宴请春客的一道主菜。
我母我姨看中那天是挖藕的好时机,姐妹俩各挑了一担竹制的专门用来挑藕的夹子,各持一把专门用来挖藕的铁锹,从皇城村阳铺岗李家大朝门出发,跨越架在碧莲河上的那座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老渡口青石板古桥,往北穿越一片布满稻桩的农田,经过几栋木板瓦屋之间一道树竹掩映的百米长廊,再走几段田间小路,就到了藕场曹家湖。
这里早在南宋末年,便是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杨幺操练水军的绝佳场所。后来因沅水卷来武陵山的泥沙,在此驻足生根,湖底逐渐升高,便演变成了湖滩,枯水时节,悠悠沅水绕湖滩而去。一代又一代湖区人抓住时机,筑起巍巍沅南大堤,使得这里成了内陆。内陆中间又夹有大大小小许多的湖泊,像从天上撒落的无数颗珍珠,熠熠生辉。曹家湖就是这其中的一颗。像其他湖泊一样,他本无名,只因曹姓人氏最早从北方迁徙来到这里,看中了独特的风水,便收住流浪的脚步,在湖的两岸,搭起芦苇棚子,安家落户,繁衍子孙,曹姓人丁多了,这里便自然而然成了曹家湖。由于曹姓人向官府缴税从不讲价钱,官方也予以了认可,无论朗州、武陵,还是常德府志中,便有了曹家湖的名字。
曹家湖的藕,以其品质优良,味道独特,享誉洞庭湖。每到冬腊两月,四周汉寿、常德、安乡,以至桃源的农民,都会从四面八方涌来曹家湖挖藕。
此时,我母我姨眼前的曹家湖,满湖的玉臂藕,不再撑开绿伞般的荷叶,也不再举起碗状般的莲蓬,而是弯下与风雨搏斗了春夏秋三季的傲然身躯,进入了冬眠时期。
我母我姨走进洋溢欢声笑语的湖场,寻觅到一片好藕凼,便挥起手中的藕锹,掀开乌黑的淤泥,接连不断地从泥底掏出一支支白花花的玉臂藕。这除了需要力气,更需要娴熟的技术,藕锹入泥,不轻不重,轻了,见不到一支完整的藕,重了,会把整支藕挖断成多节。滨湖人对挖出的藕有极其严格的讲究,那就是整支一丈多长的藕身不能有一丝藕锹划的伤㾗。专用名叫“伤锹”。如果伤锹的玉臂藕,出售,没有好价钱,送人,也拿不出手,因为他失出了原汁原味。
我母我姨挥汗如雨,身旁的藕夹里,一支支玉臂藕整齐地往上加高。
一旁有个挖藕的男子名叫龙金虎,却半天挖不出一支藕,向来欺善怕恶的他,眼红我母我姨不停地从漆黑的泥巴里抽出一支又一支白花花的玉臂藕,便挤占我母我姨的地盘。
我母亲与之理论,龙金虎平时作恶惯了,根本不把我母放在眼里。明明是我母亲手中的藕锹掀开泥巴,一支手臂粗,扁担长的玉臂藕才得以从泥底露面见天,龙金虎则撞开我母亲,强行把那支藕夺了过去,据为已有。
我大姨见此情形,火冒三丈,一步冲上去,挥起手中的藕锹,朝龙金虎脚前猛地一插。
龙金虎吼道:“好你个小女子,敢与老子动武不成?”
我大姨二话不说,朝龙金虎脸上甩出一巴掌,说:“你欺老子不敢动武?老子是李祖军的女儿,你有种就跟老子过招!”
我外祖父是出了名的“打匠”,即武功高强的人。他34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当挑夫,从皇城港行至常德的半途,他看准来水庙至苏家渡之间那片有利地形,凭借一根齐眉棍,横扫7个日本鬼子,得以死里逃生。这事传遍了西洞庭湖一带。
此时龙金虎听了我大姨的话,两眼有点发呆,两腿也微微发抖。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我外祖父的对手。
“男不与妇斗。龙金虎你抢夺李家姐妹的藕,把你的脸用裆裆小衣(内裤)装起来!”
“你那不是两块脸,是两块屁股!”
湖里挖藕的人一片呐喊声,都出于抱不平,为我大姨助威。
我大姨一手插腰,一手指着龙金虎的鼻子,大声说:“你不把这支藕还给我姐,老子就一锹请你见阎王!”
“清枝姐姐,你把他夹到胯里打!”
“看他龙金虎还要脸啵?!”
藕湖里的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
这时,我母亲对龙金虎晓之以理地说:“你看这湖里,到处都有藕挖,你偏要抢夺我们的藕凼,你没有打到一滴滴男人的气!”
我大姨对龙金虎下了驱逐令:“你滚开,这是我们的藕凼。你还不滚,老子就动手了!”
在众人的一片助威声中,龙金虎不敢与我大姨交手,只得提了藕锹,连那支藕也没有要,灰头土脸的溜到一旁去了。
从这件事,也可见我母亲与我大姨这对患难姐妹从小关系是何等的密切。这种基因遗传给了我和上林。上林的性格颇像我母亲,而我的性格则颇像我大姨。
1945年,我母亲嫁进了何婆桥的杨家,一年之后,我大姨嫁进了金鹅嘴的罗家。我父亲杨先德,我姨父罗廷贵,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都是忠厚本分人,都是农忙插田,农闲捕鱼。因而两家来往频繁。这奠定了我与上林从小互相亲近,结婚后照样亲近的坚实基础。
同一年,我母亲生育了我,大姨生育了上林,彼此相隔三个月。我是哥,上林是弟。他称我母亲姨妈,我称他母亲大姨。
小时候,我与上林,还有我表姨刘春秀的儿子万龙武,三个结伴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我的外公外婆家,因为我的外婆与万龙武的外婆是亲姐妹。万龙武出生5月25日,小我11天,小名取其出生月日的谐音叫爱武。

母亲李清凤(前排左)、大姨李清枝(前排右)、小姨李圆清(后排右)、三姨李清纯(后排中)、表姨刘春秀(后排左)合影
一次我们三个都争着放牛,弄得那头牯牛不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结果直接跳进了水塘里。外婆自然对三人中的老大提出了批评。我觉得外婆偏向上林,气呼呼扭头就走,直接冲回了位于老渡口的家。上林则领着爱武,紧追三四里路,一直追到我家里。他满脸微笑地劝说我回外婆家。他说:“哥哥你不回去,外婆就会不高兴,不高兴就会生病。难道你不害怕外婆生病?”我听了他的话,兄弟三人又一路追赶着,回到了外婆家。
上 林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小名叫阳婆,我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孩子,小名叫四婆,因为算命先生王子涵说,我俩都不好养,只有男孩女养,前世的父母找不到,才能长大成人。于是他是婆,我也是婆。
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一致认为,我俩躲避前世父母寻找的最佳办法,就是上学读书。
1965年,我考进汉寿县二中,上林为我高兴。1966年,上林考进汉寿县一中,我为他高兴。
1966年9月1日那天,我办好入学手续,便立即从县城东郊外的镇龙阁,步行三四里,赶到县城南侧的汉寿县一中,兄弟俩第一次远离家门见面,都显得格外兴奋,也倍加亲热。
1968年12月,我被推荐上聂家桥中学高一班就读。1969年12月,上林被推荐上聂家桥中学高二班就读。两个班的教室只隔一面墙,课间休息的铃声一响,我俩就会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那时都是走读,每天早晨,他从金鹅嘴到达顶岗铺三叉路口,如果没有见到我,他就会在那里等候我的出现。如果我从老渡口先到达顶岗铺三叉路口,没有见到他,我也会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我俩见面,一起有说有笑地踩着青石板铺成的古老的聂家桥,跨一片沧浪水,穿几坵农田,越几块旱地,肩并肩进入学校。放学后,我俩会一起奔跑在学校的篮球场,打完一场球,然后抹掉汗珠,踏上回家的路。抵达顶岗铺三叉路口,他向东,顺清泥湖回家。我向北,朝碧莲河而归。相互边走边挥手,直到何家湾里和彬树王家的树竹掩映了我俩的身子,彼此才不再挥手,一心往家里奔。
我俩同校一年的高中时光是愉快的。可接下来,是难舍难分地各奔一方。1970年冬季大征兵,他体检合格,穿上绿军装,走向军营。我则因有人从中作梗,未能实现当兵的愿望。我送他启程时,他一再鼓励我不要放弃,他在部队等我。
上林入伍后,我大姨特别想念他,经常独自站在门前那株如伞状的桂花树下,面对悠悠的清泥湖水,望着他向北流向沧浪河,仿佛看见她北去的儿子的英姿。这是她思念最浓的时刻。每当思念不能自拔,而深陷极度痛苦时,她就会到金鹅大队部来看看我,或是托我姨父带口信,要我上她家吃饭。
当时的金鹅大队,民兵工作做得好,被树立为全国的一面先进红旗。汉寿县委为了及时总结这里的民兵工作经验,从县里和公社抽调笔杆子,组成一个专门的驻队写作组,将这里创造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予以总结,不适时机地向全国报道推广。县里领头的是宣传组的干部刘平政,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公社派出的是本身就在金鹅大队长期蹲点的党委委员张铁成,聂家桥公社党委书记兼武装部长郭志才把我从熊家铺大队抽调出来,有幸成为这个写作组的一员。

罗上林(左)任职中共武陵区委副书记期间与原聂家桥公社党委书记、汉寿县政法委书记郭志才合影
我姨父担任金鹅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排位二把手,我便有机会经常与他一起开会,听他介绍情况。他每次与我见面都会悄悄地说:“你大姨想上林都想病了,她说看见你,就像看到了上林。散会后,你就去我家,让大姨好好地看看你吧!”我大姨家距大队部近两华里路,属金鹅大队第九队。我每次去都是扑田跑(即抄近路),恨不能一步跨进她家门。大姨见到我,第一个举动就是拉着我的手说:“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上林。太想他了,想得心里疼。”我如果隔两天没去,她就会上大队部来找我。刘平政、张铁成看到了,马上会中断我们的工作,嘱咐我好好陪大姨说说话。他俩善解人意的举动,令我终生难忘。刘平政温文尔雅,给我的印象特别亲切。张铁成则不一样,他身材武墩,皮肤漆黑,不是开会,很少说话,就像个黑包公。当地干部和群众,对他说的话都是不打折扣地照做不误。郭志才书记对他也是特别的倚重和信任。我开始报到时,就无形中对他有几分惧怕感。他对我大姨的态度,不仅让我消除了对他的惧怕,还格外增加了几分亲切感。正因为他俩能力强,水平高,为人好,不断得到组织的提拔重用,刘平政官至常德市人事局局长、市政协副主席,张铁成官至汉寿县围堤湖乡党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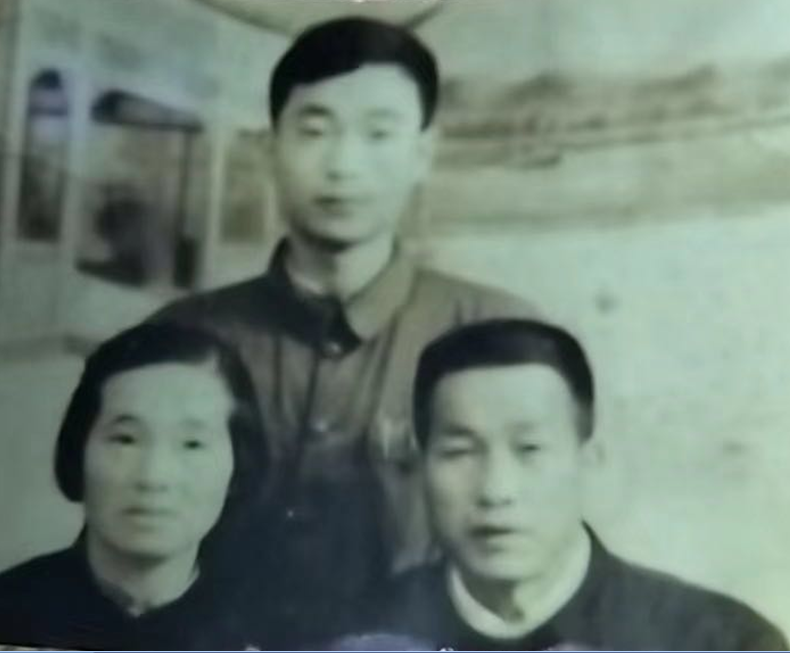
杨远新与大姨李清枝、大姨父罗廷贵1973年春在汉寿县照相馆合影
1971年11月,我被录用为国家干部,走进了汉寿县城工作。从此,距金鹅大队远了,距大姨远了。大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县城看看我,有时是她独自一人,有时是和姨父一起。大姨见到我,第一个举动依然是拉着我的手说:“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上林。太想他了,想得心里疼。”
我理解大姨的心。我便想方设法,接通远在河北邯郸市的上林所在部队驻地的电话,让他与母亲说上几句话。放下话筒,大姨抹着眼泪对我说:“要是从电话里能看到他,那就好了。”遗憾的是那时的通信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大姨的这一憧憬和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当可以视频通话了,她已离开了人间。
1974年初夏,上林经部队首长批准,回乡探亲。兄弟离别四年,终于盼来了重逢的机会,我当然抓住不放。我连夜兼程,天明赶到金鹅嘴,与他见面的第一时间,他向我递上了从部队带回的珍贵礼物。一套全新的长篇名著《红与黑》。那时要得到这样一套外国名著,十分不易。我如获至宝。几十年过去,这套《红与黑》一直随我南征北战,如今仍然完好的挺立在我的书柜最显眼的位置。见书如见人,我在书房的时光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朝《红与黑》多看几眼,这种时候,眼前就会浮现上林那英俊的身影。他那张微笑的脸,在我脑海里永存,挥之不去。
他这次探家,我给他物色了对象,但由于他尚未提干,加之家在农村,我第一次当红娘,结果失败了。我感到很歉疚,他则很大度,满脸微笑地对我说:“哥哥,我们都还没有老,还不到讨不到堂客的那一步。面包会有的,堂客也会有的。”
接下来的一次探家,他给我带回了一件崭新的军装和一顶崭新的军帽。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崇尚军人,实现不了当兵的愿望,也想有一件军装身上穿,有一顶军帽头上戴。那样也觉得无尚的光荣。我打开军装一看,竟然是四个口袋的干部服。此时的他,已经提升为排长兼连队副指导员。他还向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已经在常德市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对象,道地的常德城里人,担任基层团委书记,名叫马先春。我也带去了自己的女朋友,他和我大姨看了,都表示满意。可他回部队不久,我的女朋友和我吹了,他则与马先春发展得很顺利。也许爱情给了他动力,他很快被提升为某部营长。于是向部队首长递交结婚报告,顺利得到批准,领了结婚证。他俩在部队举行了俭朴的婚礼。那种婚后相亲相爱,美满幸福的生活,既令我羡慕,也给了我动力。我急起直追,在总结前面七次恋爱失败的教训之后,我终于与第八个恋爱对象走进汉寿县城关派出所,领取了结婚执照,继而有了自己的小家。
接下来,上林转业到常德市委组织部,即现在的武陵区委组织部工作。每年的春节,我俩都会携妻,不约而同的在正月初二这天,给外祖父外祖母拜年,兄弟相聚甚欢。外祖父称我远新,称他上林。而外祖母则一直没有改口,依然呼我四婆,唤他阳婆。我俩总是乐呵呵地回应,而且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甜蜜的称呼。
外祖父未能等到我俩的孩子降落人世,因病去世,享年71岁。外祖母则多活了11年,于1990年8月去世,享年84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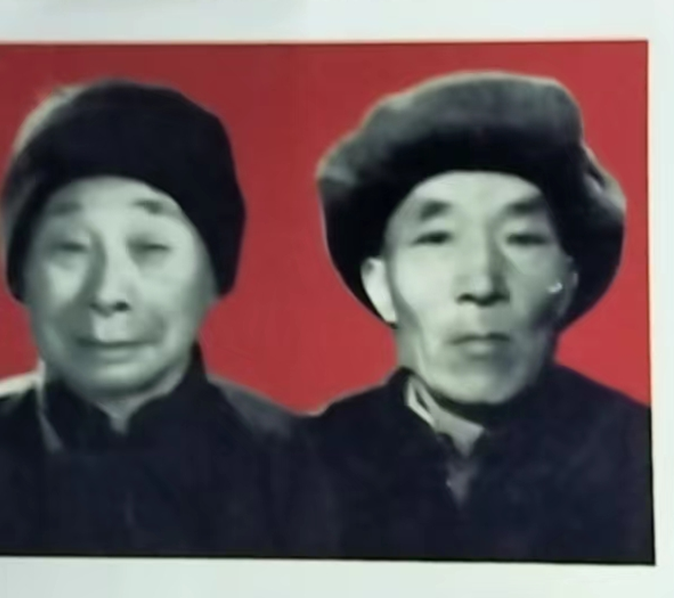
外祖父李祖军外祖母邓冬梅合影
直到始终坚持称阳婆、四婆的那个最疼爱我俩的人去了另一个世界,才没有人称阳婆、四婆了。前世的父母也不来找我们了。我俩恢复了由婆到公的本来身份和面目。
外祖母去世时,她心心念念的阳婆已是常德市武陵区委组织部秘书,她心心念念的四婆已是湖南省公安厅《当代警察》编辑部副主任。外祖母安详地合上那双曾经美丽、曾经深邃、曾经忧患、曾经矍铄的眼睛那一刻,我和编辑部另一位副主任熊剑先生正在隆回釆访金库失盗案。我连夜千里迢迢,几经转火车、转客车、转货车,风尘仆仆赶到皇城之南的阳铺岗李家大朝门时,阳婆和妻子马先春、女儿罗欣欣已先我到达。他迎上前,拉着我的手,我俩都难过得张不开嘴,把千言万语委托给了各自眼里涌流的两条小溪。我俩并排走到外祖母灵前,同时屈下双膝,同时伸出双手,同时叩下头,长拜不起。
此时此刻,外祖母为我们做的桩桩件件,化成沅水的波涛,澎湃涌来。外祖母离去后,渐渐地我俩这种相聚的时刻减少了。而在工作中相聚的时刻则增多了。
上 林不久出任武陵区民政局长,我俩同属政法口。相互工作上有了交集。我最难忘的是我委托他给我堂弟杨远忠从部队复员后安排接收单位。他根据其魁梧英俊、酷爱运动的特点,竭尽全力,向市电业局推荐。正好该局篮球队需要一名主力中锋,便乐意地接收了。
此后不久,上林升任武陵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在全省乃至全国而言,由民政局长提升政法委书记的他是首例。就客观条件而言,民政局在政法口,与公检法司比较,算是弱势部门,政法委书记多数从公安局长位置上挑选。单从这点可见,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认可。
提拔县处级领导干部的前奏,是派到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常徳市政法委率队的是副书记卢子成,一个人品和酒品堪赞的人。我接到上林的电话,立即采购了一件高度白酒,驱车省委党校,就近选择一家土菜馆,与卢子成率领参训的9位青年干部酣畅淋漓的碰杯。
上林结业后回常德,走马上任武陵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1999年,他升任中共武陵区委副书记,依然分管政法口的工作。2000年9月1日,常德发生匪徒张君团伙抢劫银行案。我从人口管理角度去作调研。他与常德市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周国忠一起接待我。我们三人是同乡,是同学,他俩同属高二班,在校时关系就很密切。这种特殊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感情,凝聚于工作中,令我们都感到十分愉快。
那一夜,案情谈完,几瓶酒喝完。临别时,三双手紧握在一起,迟迟不肯松开。我们又走到沅水北岸,沿常德诗墙从西向东参观品味,他以主人身份,介绍诗墙的产生和上榜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情况。那一夜,是我们三人走出聂家桥中学后,相聚时间最长、也是最难忘的一次。
接下来,上林改任常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在一位副市长与农林水系统几大家之间担当联络协调工作,得到各方面的好评。没想到临退休之前,一向乐观开朗,微笑面对人生的他,却突然患上了重病。开始,他并没当回事。他尽管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多年,但他一直像在部队时那样坚持早晨锻炼,身体一直结实硬朗,连头痛脑热,感冒发烧都未曾有过。直到他短时间内连续几次昏倒在了办公室,这才不得不引起重视。市政府派人派车护送他到长沙,入住湘雅二医院治疗。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表现得很乐观,无论对医护人员,还是对同病室的病友,都是以满脸微笑相待。三个月时间里,医院多次组织权威专家会诊,中西医配合治疗,其妻马先春没日没夜不离左右的精心护理,上林的病情得以好转。临出院时,主治大夫向他反复强调:休息为主,工作为辅。他却恰恰相反,工作为主,休息为辅。我得知这一情况,是在我母亲病逝期间,他带领弟弟妹妹前往我老家吊唁,其妻马先春背着他告诉我的,希望我能劝劝他。我劝他严遵医嘱,细水长流。他对我说:“哥哥!你我明年都要退休了,在有限的在岗时间,多做一点工作,退休后就可以一门心思把身体搞好。”我觉得他讲的很在理,引起我的共鸣,便不再多劝。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再次复发,并有所加重。他再次入住湘雅二医院,院方则向家属建议:速转北京治疗。其妻马先春毫不犹豫,果断决定,护送他进京,选择部队一家名牌医院,经检查确诊,专家很快拿出了治疗方案。
上林在京入院的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买好了机票,4月25日飞抵北京,直接从机场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正在进手术室。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不等我进京去看望他,2013年4月19日10时,他不幸病逝于北京,享年60岁。我得知这一噩耗,心如刀削,悲痛万分。
我和表弟李永胜,还有他在部队的一位张姓战友,从长沙驱车赶往常德,车过谢家铺时,周国忠已经在常长高速第11个出口等候。我俩见面,相互眼眶潮湿。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三人曾经的约定,退休后都回到老家聂家桥乡,上林在清泥湖北岸,我在老渡口古桥南岸,国忠在武峰山东侧,各自整修祖传下来的老屋,一起过解甲归田的诗意生活。三方约定再也难以兑现了。顿时泪水冲决大坝,沿鼻沟哗拉而下,重重地砸到脚上。
走进追悼会现场,我小姨李圆清一步冲上来,双手扶住我的肩,放声痛哭。上林生前,每逢过年,都会携妻女,到清泥湖水注入沧浪水一侧的高凡村,给小姨一家拜年。小姨家每遇困难,只要他得知,都会尽全力相帮。这怎不令小姨痛心。
在上林的追悼会上,我看见一位50多岁的妇女,大声痛哭地走进灵堂,扑到灵柩上,一双泪眼端详着棺内上林的遗容,撕心裂肺般地哭喊道:“罗书记呀!你是个大好人呀!你为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可老天爷不公,不给你长寿!老天爷真是瞎了眼啦!”接着她双膝跪在马先春面前,痛悔不迭地说:“罗书记住医院我不晓得,我没有去看望他这位大恩人,我这一辈子都后悔不完。”
常德市政府为上林举行的追悼会上,一位市领导致悼词,满含深情地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和高尚人品。尤其对他任武陵区委副书记期间,把下属单位和个人吊唁其父母赠送的礼品礼金,顶着压力,毫不动摇地全部如数退回的廉洁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
常德市委督办专员周国忠,代表亲友,回顾了上林奋斗的一生。
家乡金鹅村的村支两委全体成员,和村民委派的代表,一起赶到追悼会上,送别上林最后一程。他们流泪数说建设村级路网和村级电网的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是上林自掏腰包,并四处筹资,帮助渡过难关,成为全乡第一个所有村民小组通水泥路、通民用电的先进村。乡亲们说到这些,不禁放声悲哭。
上林去世后的这十年里,我从未将他忘怀,他那张微笑待人的脸,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多少回梦里与他相聚,醒来泪流满面。
2014年4月29日、5月15日,我乘车过邯郸,联想起上林所在部队曾经驻扎在此地的情景,难以抑制对他的思念之情,写下了一首小诗:
车过邯郸忆表弟罗上林
一
应征入伍驻邯郸,
劈岭开山筑路难。
军营最苦工程兵,
却在信中尽道甜。
姨母思儿难抑时,
视我为弟搂胸前。
千里探家载誉归,
英武豪迈已军官。
二
正当盛年转地方,
半生武陵作奉献。
局长书记秘书长,
民政政法主全盘。
除暴安良护百姓,
尊师爱友孝堂前。
可恨病魔突缠身,
华佗无奈手足断。
我特别将此诗收入了《杨远新文集》,以留作永恒的纪念。
(感谢罗荣建提供文中图片)
2023年1月3日草稿于柯克兰德18195号
2023年2月26日二稿于里加奥德211号
2023年4月13日定稿于里加奥德211号

作者杨远新近照
【作者简介】:杨远新,湖南汉寿县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湖南省首届公安文学艺术协会秘书长、湖南省公安文联理事。迄今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18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与杨一萌、陈双娥合著)《百变神探》《爱海恨涯》《东追西捕》《拟任厅长》《红颜贪官》《春涌洞庭》,中篇侦探小说《特区警官》《惊天牛案》;中篇纪实小说集《中国刑警大扫黑》《中国刑警在边关》,长篇儿童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险走洞庭湖》(与陈双娥合著)《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中短篇儿童小说集《落空的晚宴》《今夜,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长篇报告文学《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创造奇迹的人们》《奇人帅孟奇》《县委书记的十五个日日夜夜》《走进福山福水》《天有巧云》等,201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8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首届一等奖、二届二等奖、三届三等奖、四届二等奖,文化部和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颁发的编辑奖、湖南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首届儿童文学奖等各类奖项58次。散文《我的祖母》被编入大学教材,分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