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望
许海涛2021-01-03 09:25: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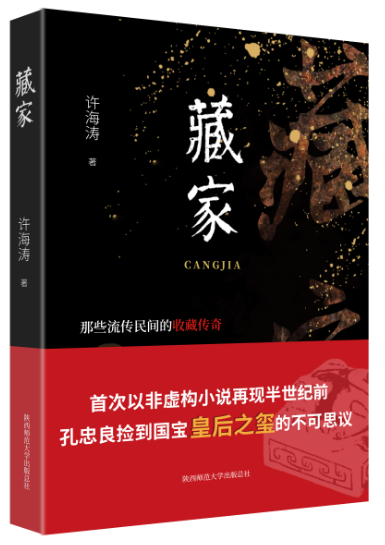
窥望
——《藏家》自序
作者:许海涛
马家窑村旁的大陵,是我的瞭望之地。
马家窑村东半里,蹲踞大陵。南一箭远,“藏掖”殡仪馆——半坡上,崖势和树木掩着,真像藏着掖着呢;老早时候是乱葬坟,杂乱拥挤,像大杂院。北二里,与王车村连畔种地。王车村,乃“王”曾驻辇之地。哪一尊“王”?没人说得清白。西,隔公路,与黄家窑村相望。跟马家窑一样,老早时候,黄家窑也是乱葬坟。
马家窑咋这样憋屈,让鬼魂围了?
大陵下,乱葬坟中,殡仪馆里,都是鬼魂啊!
先有大陵,后有乱葬坟,再后有马家窑,最后才有殡仪馆。
有位姓黄的洛南长工,扛活安了身,依二道原旋窑安家,遂有黄家窑。姓黄长工的同村乡党,姓马的,扛活也安了身,平地凿穴,穴内旋窑——这样的窑叫地坑窑——便有了马家窑。黄家窑坡势陡,可旋窑;马家窑坡势缓,旋不得。咋不盖房呢?
原上有的是黄土,长工有的是力气啊。
活人与鬼魂睡在一搭,怕不?
洛南遭大灾,逃不出来,死;逃出来,生!死里逃生了,还怕啥?窑里容了身,往前推日子。
我爷为啥在乱葬坟置地安家?
我爸说道:“做买卖不稳当。先人说,原上黄土厚,庄稼旺,日子稳当些。”
在地里做得直不起腰,我爸怨道:“稳稳当当下笨苦啊。”我跟在我爸后头,也做得直不起腰,想去问我爷:“放着城里的舒坦日子不过,咋让后人受这个罪?”
往哪儿问我爷?我降生马家窑的时候,我爷已经睡在黄土深处的黑堂里了。我爷花了多少钱,买谁的几亩旱地,我爸不知道。我爸说道:“你爷说,往东北方向走四百里,过黄河,进山西,那儿是咱的根。”
山西啥地方?
我爸答不上来。
我爸只记得他生在河南街;只记得他长在谷家巷,在窄窄的巷子里滚铁环;只记得我爷的买卖是租赁花车,像如今的豪华婚车,却鲜有“发斯”;只记得我爷给他吃猪尾巴,一手油,一嘴油,再没有那样的香了……我爷卖了花车,做起了卤肉的营生;只记得他在果子市上小学,果子市有果子铺,棉花铺,粮食铺,油铺……
我们的根在哪里,我爸记不得了。
我长大了,不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我儿子降生了,更不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天色清朗空明,爬上覆斗顶——大陵像巨大的覆斗——我四面瞭望。南面,长长的、大大的山像挪移了,云雾缭绕,就在眼前,纵身跳,能跳到云彩上。云彩一朵又一朵,驮得了马家窑村七十七口人。挖地坑窑的马爷,佝偻腰,吭哧吭哧也爬上了覆斗顶,捋一捋被风吹乱的白胡子,指点着白云,对我说道:“东南那一大坨白云底下,就是洛南,我屋在柴峪沟,沟里的野毛栗子,又面又甜……”我没有被野毛栗子诱惑,还是专心找河南街。正南,河的南岸,数不清的村庄,我难以确认哪一座村庄是河南街。我又找谷家巷。谷家巷在河的北岸,咸阳城里,街巷纵横,房屋鳞次栉比,我难以确认哪一条巷子是谷家巷。我朝东面瞭望,想看见黄河,更想看见黄河对岸的山西,却看见一疙瘩又一疙瘩大陵。我瞭望西面,又看见两疙瘩大陵。大陵间,散落大大小小的村庄。我爸说道:“刨到根儿上,马家窑只有七户人家。”这个根儿,指马爷挖地坑窑后的十年间,之后,实行集体化,再没有人家迁徙来。再之后,一九七六年,迁移了些半坡的乱葬坟,有了殡仪馆。
之前呢?
七户人家落户马家窑之前的根呢?
除马爷记得清他出生在柴峪沟外,其他人,说得清的只是遥远的县名。村名呢?像离离原上草,被野火烧光了。
我迷茫。
我爸说道:“活下来的就是根!”
我不这样想。我想,根在深处,在黑暗里,像草的根,树的根,庄稼的根。
朝北面瞭望,还是山,与南面的山一样,我不知道山的名字,像旁人一样,叫南面的山南山,叫北面的山北山。北山的山梁,朝一个方向攒着劲儿,那劲儿似乎把控了每一块山石,每一棵树,每一株草,甚至每一朵云,从四方,朝中央一浪一浪奔,猛然间,拔高,凸起,直直向上,像高高擎起的火炬,直插云天。
一回又一回,一年又一年,我爬上覆斗顶瞭望,瞭望……瞭望到了什么?河南街从没有得到过确认。谷家巷也从没有找见过。从未望见过黄河。从未望见过黄河对岸的山西。只看见一疙瘩又一疙瘩的大陵,大陵间散落的村庄,不变样子的咸阳城……
西北风吹着,东南风吹着,我一天天长大了。
到了该知道的年龄,我知道了南面的山叫秦岭,河南街和谷家巷之间的河叫渭河。我知道了大陵叫作延陵,赵飞燕、赵合德姊妹俩侍奉的汉成帝刘骜埋在覆斗下。我知道东北方向一疙瘩又一疙瘩的大陵,是康陵、渭陵、义陵、安陵、长陵、阳陵,西面的两个大陵是平陵、茂陵。这些陵下,埋的都是刘骜家的人。有他的长辈,也有他的晚辈。我知道了二道原叫作五陵原。南山和北山间,东西八百里,叫作关中。我知道了北面的山是九嵕山。“火炬”顶端,是昭陵,埋葬着李世民。我知道了昭陵西北方有乾陵,埋藏武则天和他的丈夫李治。昭陵东,绵延二百多里的山势间,有献、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贞、简、靖十六座唐陵。陵下,埋的都是李世民一家人,有他的长辈,有他的晚辈。
有人说,刘家的陵下,是刘家的根;李家的陵下,是李家的根,都像大树的根,深深扎在黑暗里,看不见。还有人说,那不仅仅是刘家的根、李家的根,还是更多人的根,民族的根。
他们说的似乎不错。
九十三岁的马爷死了。他唯一的愿望是把他埋在洛南的柴峪沟……马爷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无法满足他的愿望。马家窑一百二十二口人也无法满足他的愿望。这时候,马家窑已经一百二十二口人了。即使埋在火葬场东墙外的乱葬坟,为他堆起一疙瘩黄土,立一方青石的墓碑,这样的想法也实现不了。乱葬坟早已不准许土葬,最后,终于……马爷被推进了火化炉,高高的烟囱冒出浓烟,向东南方飘去,飘向秦岭……我望着飘游的白云,默默祷念:“马爷,风长眼呢,你会回到柴峪沟!”
马爷的根在柴峪沟吗?
像草的根、树的根、庄稼的根,柴峪沟地下的黑暗里,有马爷的根吗?
在河南街,在谷家巷,在黄河,在黄河对岸的山西,在土地深处,黑暗里,像草的根、树的根、庄稼的根,有我爸、我、我儿子的根吗?
我想看见!就像我爬上覆斗顶瞭望,想看见与从前有关的一切。
王车村北二十里,一院幸存的老宅里,我看见了上千幅 “容”,色彩鲜艳,神情端庄。“容”是先人像,老早时候,悬挂在中堂,或是祠堂。
在辘轳把巷的一家老房里,我看见了三百多枚印章,铜的、骨的、玉的、寿山石的、象牙的、黄杨木的……从战汉到民国,跨度三千年。辘轳把巷与谷家巷隔一条大街。爬上谷家巷口的楼顶,我望见了马家窑,望见了汉成帝延陵。马家窑像一枚草叶。汉成帝延陵像一粒土坷垃。
在渭河南岸一个叫做六村堡的村子,我看见了上万枚瓦当,有云纹的、水涡纹的、树叶纹的,有刻“汉并天下”的,刻“长乐未央”的,有刻“上林”的……我问主儿家咋有这么多,他笑道:“这儿是汉城遗址,这些瓦当都是咱先人房檐上的呀。”还有陶的猪、牛、羊、鸡,陶的粮仓、灶、釜、盆、瓮……他说道:“这些都是咱先人的家当啊!”
在秦岭北麓,一个叫做南五台的地方,我看见了近万根拴马桩,有辈辈封侯的,有太狮少狮的,有胡人驯兽的……五六百年、三四百年流传下来,挺立旷野,像兵马俑巍巍方阵一般震撼人心!主儿家说道“拴马桩不光用来拴马,还是咱庄户人家的华表呢!”
在黄河岸边,距离鲤鱼跳龙门不远,一个普通的庄户人家,我看见了五万多本老书。早的到明代,晚的到“文革”,堆垒满屋,难以插足。主儿家不善言语,见我惊诧地喊叫,只咧嘴憨憨地笑……
在五陵原,在关中,在山西,我还看见了五千多份老契约、三千多幅老绣品、两千多套老皮影、一千多本老课本、八百多本老日记、五百多帧老照片、三百多张老条案……
哎呀,数不清的老器古物,在数不清的人手上。
他们在干什么?
寻根!
寻得到吗?
能!
他们说,寻到了先人的一幅画,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当,就寻到了根。
这,这算寻到了根吗?
他们说,算啊!一幅画,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当,像根须,传到如今,还活着,意味着根还活着啊!
根还活着吗?
一叶窥秋,窥斑见豹,一幅画,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当,就是叶,就是斑!
于是,我成为他们的徒弟。
他们被唤作“跑家”,深潜乡下,挨门进户搜罗先人的遗存,早的,更早的,老早的,更老早的先人遗存,越早越欢喜,越老越珍爱。跑得久了,跑下了规模,便被尊为“藏家”。
一丝丝根须在藏家手里聚拢,滋养起一条庞大的根系,滋养我的干渴和迷茫。
我不再爬上覆斗顶瞭望。瞭望给我的,只是迷茫和叹息。
我开始窥望。窥望一幅画、一行字、一枚印、一件家当,像透过孔隙,窥望我爸、我、我儿子的根,马爷的根,马家窑的根,黄家窑的根,王车村的根,刘家的根,李家的根,乱葬坟下的根,或许,一个民族的根……
作者简介:
许海涛,1969年生,陕西咸阳周陵人,著有短篇小说集《跑家:那些埋藏民间的古董传奇》、长篇小说《残缺的成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