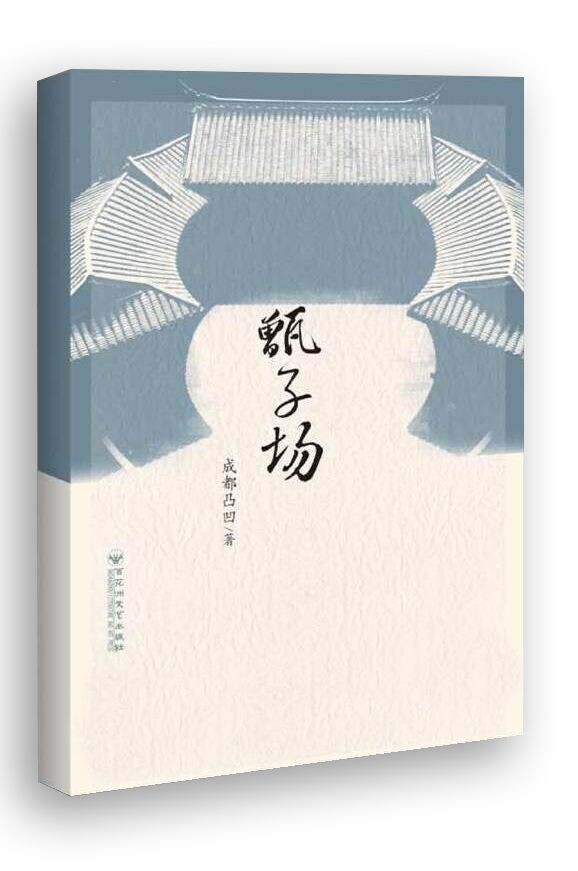凸凹长篇小说《甑子场》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家网2014-11-12 16:51:13
诗人凸凹长篇小说《甑子场》出版
故事发生在成都东山地区一个迷雾缱绻、石头会说话的客家小镇。
从解放后到土改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对新政权和一群陌生人的突然闯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荷锄桑野的农民们,睁大了茫然的眼睛。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护送他去某国大使馆赴任的一个加强班,途经成都郊外龙潭寺乡时,被叛乱分子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肚、凌迟惨杀,史称“龙潭寺惨案”。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战斗在全国打响。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镇甑子场为中心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长篇小说《甑子场》以“龙潭寺惨案”和洛带镇“三三叛乱”以及叛乱发生前后的诸多真实信息为背景,将故事整合、锁定在一个政权更迭不断的场镇“龙洛镇”上,以历史和现实相互穿插的回环结构,传奇而又真实地讲叙了中国解放初期大背景下,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的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的男人之间的温软而残忍的独特情感博弈。在变天与反变天的血腥博弈中,又切转出了桃花与罂粟花的故事。而变天与反变天的历史记忆,又是从当下变地与反变地的对峙与冲突中牵扯而来……
一个女人指二十岁的美丽地主婆扣儿,三个带枪男人指从小追求扣儿的长工、叛乱首领鱼儿,六十岁的镇长、自卫大队总指挥安,年轻革命者、公安科长禾,一个不带枪的男人指扣儿的首任丈夫、地主蛋。
在《甑子场》的书页翻卷声中,至今鲜为人知的罩在国家级重大史实上的氤氲迷雾,至此尘埃落定。
清洁、诗意的语言表达,独到而睿智的叙述方式。对人性与心灵近乎恐怖的开掘,对命运与疼痛近乎死亡的关怀。扣儿、安、禾、鱼儿、蛋,这些小人物在一个小镇上的逗留、来去,颠覆既往言路的同时,碎片醒来,重新拼合成一九五零这个特殊年份的国家镜像……
《甑子场》完成于2011年10月,是诗人成都凸凹的小说处女作。
《甑子场》,成都凸凹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37万字,定价37元。当当、亚马逊、京东有售。
[我读《甑子场》]
《甑子场》傍依一个客家小镇启动和开展一场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读来我竟不能肯定它是不是时下所谓的“非虚构小说”。说它是纯粹的小说吧,它在建构纯粹的文学性的同时,其事体又有一种真实的模糊镜像。说它是田野实录吧,无论是结构、叙述、语言,还是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插的故事的处理,又有一种书卷气浓郁的先锋文学的光泽与质地。
多文类、多文体的搓揉与黏合,复合逻辑的立体美学呈现,应该是凸凹对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在一个方面的贡献。
——何开四(著名文艺批评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的创作走险,是对长篇小说生成经验的一个贡献。
——著名批评家、《中国作家》副主编程绍武
《甑子场》借一个客家小镇上一位女人与四位男人的故事,把一宗硬邦邦的国家事件,进行了柔软的美学化与小说化处理。正是在这一“化”的过程中,凸凹精致而诗意地呈展了自己的小说理想。《甑子场》对中国小说写作格局可能性的拓动与作为,正是凸凹小说理想的落地与坐实。
——傅恒(著名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是一部诗意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诗意与现实主义是一个悖论,或者说,诗意天生是反现实主义的。但《甑子场》的叙事实践表明,悖论的两极在文学文本的叙事艺术中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甑子场》讲述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当然更是现实的历史故事。在讲述中,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展开对历史的想象性表达,在意象、隐喻的叙事层面将历史寓言化,奇幻化,使那些史实材料在意象话语中获得了神奇的再现,历史也在诗境中重现,而人物性格及命运也在悲壮的诗境中载沉载浮,有一种雕塑感。
与此同时,叙事结构奇诡而循环,像一首回还往复的咏叹调,不断地从现在回到过去,又从过去回到现在。这种以各个人物为叙事视角来展开的叙事结构,是一种复调的叙事艺术,具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觉,从容舒缓,张弛有度。
从历史理念上看,《甑子场》对历史和人物的处理,也同现行的主流历史小说构成了对话乃至挑战的关系,隐喻着一种新的历史理念。
——向荣(新锐小说批评家、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历史和时代精神,不是通过文学反映出来,而是通过文学确证下来,凸凹的长篇小说《甑子场》,就是一部解构和确证的作品。解构本身即是确证。凸凹本是个优秀的诗人,诗人的天职,便是追求卓越。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
《甑子场》构思很有想法。“关注人的终极命运”,是看了这个小说后的感想。许多细节新鲜而独到,这是作者作为诗人的优势,想象的优势。作者的写作理想,以及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感,显而易见。
——罗伟章(著名小说家、巴金文学院创作员)
《甑子场》很中国,很洋气,很史诗。
——新锐小说家、《当代》杂志编辑石一枫
凸凹君“潜伏”成都龙泉驿算来怕有二十来年了罢,像福克纳回到他“邮票大小”的家乡一样,凸凹君选择成都东郊这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施行他的笔耕,我是他诗文的拥趸,他那些如同“包谷酒嗝打起来”似的乡土诗文,使我们看到了滚滚红尘之外另一种坚持与展射。龙泉驿是明王陵与客家人聚居区,触处无不有惊奇,有吊诡,有诗。现在凸凹君献出了他的一卷新作,也是他第一个长篇小说,《甑子场》既是历史的画卷,也是他自己求新求变的一个猎奇。在这个古镇上,小民走过,老财走过,义士走过,淑女走过。惟不走过的,是这方泥土,这只地球上万万万分之一的一杯风水。
读这卷小说,要买花生米下酒,同时要食洛带镇驰名的“伤心凉粉”,在惊奇动感的瞬间,一拭铅热之泪。泪水花了美人的颜,湿了壮士的须,亦然滋润了文艺的心……
《甑子场》力图刻画一个客家小镇的历史风云,将作者近些年的生活体验感觉集中表现,熔于画面,行文如行云流水,展示了作者写作高手的精湛功力与结构能力。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张放(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甑子场》的题材是重大的,情节是戏剧性的。诗人凸凹以诗的情怀,将其笔下的人物置于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凸显出人的命运这个大主题,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时空纵深。
“她一生中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有过感情纠葛,但这四个人都死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部小说的“点”,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与卖点。
——何小竹(著名诗人、小说家)
《甑子场》是一部向史诗致敬的小说。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命运,经由作者细腻的文字,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它既关乎爱情,也关乎人伦。变天是时代,是历史,是生存于其中的芸芸众生谁也阻挡或改变不了的既成事实。甚至,他们也无法左右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随波逐流,他们没齿不忘。而这一切,只因作者在抒写两个字:人性。因此,我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好小说。
——聂作平(著名作家、诗人、《四川文学》杂志编辑)
小说写到今天,似乎到了难以跨越的地步,困惑、迷茫一直侵扰着作家们,《甑子场》的问世,预示着另一种写作式样的可能。作为诗人的凸凹以诗性的语言对僵硬的小说叙述模式进行了一次革新,而作为作家的凸凹则以奇特的构思对传统小说文本进行了一次破坏。不能不说,小说《甑子场》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制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诗人、作家徐甲子
《甑子场》以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和多舛命运为故事脉络徐徐展开,穿越61年的时空隧道,抽丝剥茧般为读者揭开了一层层历史迷雾。如果说三个带枪的男人与一个不带枪的男人的对比几近严酷,三个带枪男人的彼此对比几近惨烈,那么四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复杂纠结更是触目惊心!
《甑子场》始终锁定龙洛客家古镇这一核心坐标,依凭社会更迭的特殊时段和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勾连穿插、辐射显形,但并非沉浸于单一、刻板、表浅的还原和复述,而是钩沉矛盾背景,矫正形态向度,放大情感元素和生活细节,深度挖掘人情的厚与薄、重与轻,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人世的荣与辱、恒与变。精巧缜密的构思,大胆奇妙的想象,张扬不羁的叙陈,诗意恣肆的交织,吊诡迷离的悬念,成就了洋洋洒洒30万言《甑子场》的异质、独特和精良。
——诗人、作家印子君
面对影响国家和地区命运的大事件,面对那些日渐隐退的风云和传奇,成都凸凹力图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创造”历史,即“创造”“在历史的漫天尘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的小人物”的历史。所以,他既是在写六十多年前那件“大事”,更是在写“大事”中人性的善恶、欲望、真情。如此,成都凸凹以他高超的小说技艺,为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小说阅读体验。
——70后作家、《成都晚报》记者杨不易
[《甑子场》后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东北边一个叫石板滩的地方,整编集训国民党投降部队时,接到一纸调令。调令要他立即启程回成都军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报到,之后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某国大使馆武官。
朱向璃及护送他回成都军部的一个加强班,途经龙潭寺乡时,被数千叛乱分子武装拦截,遭到惨无人道的开膛剖肚、凌迟杀戮,史称“龙潭寺惨案”。惨案发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蒋介石从成都凤凰机场(亦有新津机场之说)飞去台岛不到两个月,距成都解放仅39天。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剿匪战斗正式打响;自此,平叛与剿匪这对硬词,浩大而血腥地嵌进了中国历史书写,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为腹心,龙泉、龙潭寺、西河、黄土、三岔、石盘、贾家等乡镇为依托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刘惠安是民国洛带的末代镇长,也是共和国洛带的首任镇长。《龙泉驿区志》载:刘惠安两度兼任金堂、简阳、华阳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民国政府军队路过洛带甑子场,未经他许可,不准进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边的灌县(今都江堰),后来随母去了大巴山中的万源,再后来又移居到成都平原东边的龙泉驿。以上史实,就是我移居到龙泉驿后知道的。
洛带镇隶属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潭寺亦与龙泉驿接壤。即或这样,我也是移居到龙泉驿七八年后才知道的。具体说来,我是看了《成都市志》、《龙泉驿区志》、《简阳县志》、《用鲜血建立和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简阳平息“三·三暴乱”追述》(载简阳市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简阳市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简报》)、《龙泉剿匪记》(傅全章撰写,中共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等资料,以及在写作《花蕊中的古驿》、编选《龙泉驿民间文学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图书,编剧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改编自刘晓双同名长篇小说)过程中,才逐渐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数龙泉驿人,更大多数成都平原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国人,以及异邦的同类呢?
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文字、声像和一季一季涌至的时间落叶,覆盖了最初的非时间落叶。记忆在覆盖中探出头来,朝令夕改,又像万花筒:它是个人的记忆式态,也是集体的记忆肖像。不可靠,是记忆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只消过去三五年,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记忆。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对此,我感到落寞、悲凉和无语。多年来,我一直深怀着这样的感觉。
仅仅是为这种感觉找到出口,仅仅是为排遣这种感觉,我竟自有了试图从时间落叶中拽出那段历史、还原那宗事件的念头和劲头。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就是不关心一切,也应当去关心碰巧出现在身边的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的漫天尘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的小人物。况且,抽丝剥茧,拨雾见日,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与道德使然。
说了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吗——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为什么迟迟动不了笔?显然,对于“拽出”和“还原”,我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很多时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后果,更是对肤浅与轻狂的诘责与惩罚。
小说需要细节与写点,前者是小说的“小”,后者是小说的“说”。这些,我还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们还不能说服我,更不能说服读者。
我不愿意在想象中寻找。我不愿意寻找到的东西,不接“地气”、不带“人味”。
我一直在刨食
岷山,巴山
现在到了龙泉山
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
世界上居然还存在一处
不刨食的地方
饭,张嘴就来
水,呼气即至
不见一丝丝柴禾却周身尽暖
纸是包不住火的
没关系
包不住就包不住吧
把这地方端进书中
会不会
刨刨书,满纸都是麦浪、稻香?
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
即或虚构一个小镇、一处气场
也有欢乐的惊慌
这首《甑子场》,是多年闲来无事游移无助日子,对我唯一的馈赠。
终于在残黄的史海中捞出了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的一段讲述文字:
“朱向璃被害史称‘龙潭寺惨案’,领头者就是当日上午围攻公安干部的乌杰。此事缘由还得从头一天说起,龙潭寺一个中年妇女到成都市区公安十三处报案,说她的女儿被当地恶霸徐银生抢走并囚禁在其家中。徐银生又伙同另一个头目巫杰找上门来,将与她女婿黄德兴同住一室的居民高云打死,黄亦被打伤,因装死才幸免于难。2月5日清晨,公安分处派出几名公安人员前往龙潭寺调查此案,并打算解救被囚禁的黄妻。不料,遭到乌杰等煽动的百余名叛匪围攻……”
老实说,我对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记忆中的“2月5日清晨”,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我一点不怀疑他记忆中那个“中年妇女”的女儿。
正是这段讲叙文字中的“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让我找到了小说的“小”和小说的“说”。
“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生发了这个小说又救了这个小说的命!
“她”就是小说的第一主角扣儿。有了扣儿,也就有了“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我把“龙潭寺”和“洛带”揉在一起,虚构了一个镇名“龙洛”;我把“龙潭寺惨案”故事植入龙洛,把“三三叛乱”故事及洛带场景叠合在甑子场;将洛带镇长刘惠安作为安的原型,龙潭寺叛乱头目乌杰作为乌的原型,军统成都特务头子李才干作为菜的原型,国民党残匪马力作为马的原型……我就做了这些活儿。
对于我做的活儿,诗人作家席永君评价说:“美国人以胶卷镜像还原历史,凸凹以小说文本创造历史。这是一种绝妙的互文关照。”
席永君先生提到的美国人,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1907-2004)。卡尔•迈当斯1941年夏天沿成渝公路,从重庆到成都途经并逗留龙泉驿期间,拍了百余幅龙泉镇、洛带镇甑子场照片——本书采用的正是这些照片。感谢卡尔•迈当斯为我们拍摄了这些精美、珍稀的照片!
这是一本历史小说还是当代小说?爱情小说还是战争小说?玄疑侦探小说还是诗性寓言小说?跨文本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新写实派小说还是魔幻现实派小说?爱恨情仇还是政治幻觉?乡村叙事还是城镇物语?史诗呈现还是底层书写?……
所有的好小说都是无法归类的。但愿此论是对这本小说的量身定做。
这本小说取过很多名字:《平叛1950》《变天》《桃花与罂粟》《一变再变》《一九五○年的爱情》《桃花1950》《唇上的天气》《第一枪》《叛乱》《枪》《天气》《桃色》《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完后发问,怎么可以这样写“平叛”这类重大事件和严肃题材呢,怎么可以这样叙述一个小镇的传奇故事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于小说/艺术创作/创造而言。
是啊我就这样写了。所幸,还发现了“理想的读者”。
写这个《后记》时,掐指一算,我移居龙泉驿、回归成都平原,已整整二十个年头。
这本书也许什么都不是,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是一条活过来的脐带。有了这条脐带,我与龙泉驿、与都江堰、与成都平原,才算真正粘连在一起了。
窗外阳光顺畅
山上桃花丁当
扣儿婆婆洛带晒太阳
马儿跑哇汽车唱
土著爹哇客家娘
扣儿婆婆笑笑真漂亮
2012/3/29,凸凹于成都龙泉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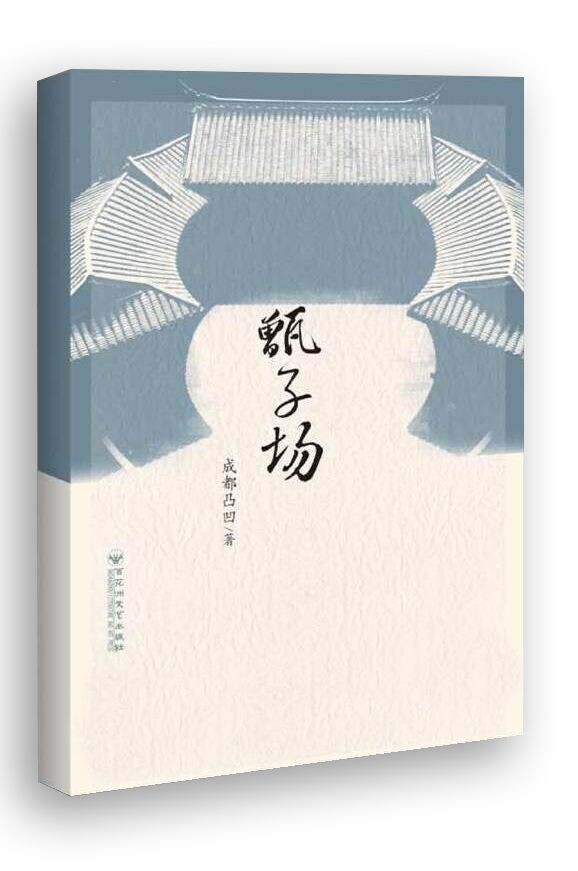
故事发生在成都东山地区一个迷雾缱绻、石头会说话的客家小镇。
从解放后到土改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对新政权和一群陌生人的突然闯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荷锄桑野的农民们,睁大了茫然的眼睛。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护送他去某国大使馆赴任的一个加强班,途经成都郊外龙潭寺乡时,被叛乱分子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肚、凌迟惨杀,史称“龙潭寺惨案”。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战斗在全国打响。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镇甑子场为中心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长篇小说《甑子场》以“龙潭寺惨案”和洛带镇“三三叛乱”以及叛乱发生前后的诸多真实信息为背景,将故事整合、锁定在一个政权更迭不断的场镇“龙洛镇”上,以历史和现实相互穿插的回环结构,传奇而又真实地讲叙了中国解放初期大背景下,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的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的男人之间的温软而残忍的独特情感博弈。在变天与反变天的血腥博弈中,又切转出了桃花与罂粟花的故事。而变天与反变天的历史记忆,又是从当下变地与反变地的对峙与冲突中牵扯而来……
一个女人指二十岁的美丽地主婆扣儿,三个带枪男人指从小追求扣儿的长工、叛乱首领鱼儿,六十岁的镇长、自卫大队总指挥安,年轻革命者、公安科长禾,一个不带枪的男人指扣儿的首任丈夫、地主蛋。
在《甑子场》的书页翻卷声中,至今鲜为人知的罩在国家级重大史实上的氤氲迷雾,至此尘埃落定。
清洁、诗意的语言表达,独到而睿智的叙述方式。对人性与心灵近乎恐怖的开掘,对命运与疼痛近乎死亡的关怀。扣儿、安、禾、鱼儿、蛋,这些小人物在一个小镇上的逗留、来去,颠覆既往言路的同时,碎片醒来,重新拼合成一九五零这个特殊年份的国家镜像……
《甑子场》完成于2011年10月,是诗人成都凸凹的小说处女作。
《甑子场》,成都凸凹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37万字,定价37元。当当、亚马逊、京东有售。
[我读《甑子场》]
《甑子场》傍依一个客家小镇启动和开展一场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读来我竟不能肯定它是不是时下所谓的“非虚构小说”。说它是纯粹的小说吧,它在建构纯粹的文学性的同时,其事体又有一种真实的模糊镜像。说它是田野实录吧,无论是结构、叙述、语言,还是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插的故事的处理,又有一种书卷气浓郁的先锋文学的光泽与质地。
多文类、多文体的搓揉与黏合,复合逻辑的立体美学呈现,应该是凸凹对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在一个方面的贡献。
——何开四(著名文艺批评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的创作走险,是对长篇小说生成经验的一个贡献。
——著名批评家、《中国作家》副主编程绍武
《甑子场》借一个客家小镇上一位女人与四位男人的故事,把一宗硬邦邦的国家事件,进行了柔软的美学化与小说化处理。正是在这一“化”的过程中,凸凹精致而诗意地呈展了自己的小说理想。《甑子场》对中国小说写作格局可能性的拓动与作为,正是凸凹小说理想的落地与坐实。
——傅恒(著名小说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是一部诗意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诗意与现实主义是一个悖论,或者说,诗意天生是反现实主义的。但《甑子场》的叙事实践表明,悖论的两极在文学文本的叙事艺术中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甑子场》讲述的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当然更是现实的历史故事。在讲述中,作者以诗化的语言展开对历史的想象性表达,在意象、隐喻的叙事层面将历史寓言化,奇幻化,使那些史实材料在意象话语中获得了神奇的再现,历史也在诗境中重现,而人物性格及命运也在悲壮的诗境中载沉载浮,有一种雕塑感。
与此同时,叙事结构奇诡而循环,像一首回还往复的咏叹调,不断地从现在回到过去,又从过去回到现在。这种以各个人物为叙事视角来展开的叙事结构,是一种复调的叙事艺术,具有一种音乐的节奏感觉,从容舒缓,张弛有度。
从历史理念上看,《甑子场》对历史和人物的处理,也同现行的主流历史小说构成了对话乃至挑战的关系,隐喻着一种新的历史理念。
——向荣(新锐小说批评家、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历史和时代精神,不是通过文学反映出来,而是通过文学确证下来,凸凹的长篇小说《甑子场》,就是一部解构和确证的作品。解构本身即是确证。凸凹本是个优秀的诗人,诗人的天职,便是追求卓越。我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
《甑子场》构思很有想法。“关注人的终极命运”,是看了这个小说后的感想。许多细节新鲜而独到,这是作者作为诗人的优势,想象的优势。作者的写作理想,以及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感,显而易见。
——罗伟章(著名小说家、巴金文学院创作员)
《甑子场》很中国,很洋气,很史诗。
——新锐小说家、《当代》杂志编辑石一枫
凸凹君“潜伏”成都龙泉驿算来怕有二十来年了罢,像福克纳回到他“邮票大小”的家乡一样,凸凹君选择成都东郊这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施行他的笔耕,我是他诗文的拥趸,他那些如同“包谷酒嗝打起来”似的乡土诗文,使我们看到了滚滚红尘之外另一种坚持与展射。龙泉驿是明王陵与客家人聚居区,触处无不有惊奇,有吊诡,有诗。现在凸凹君献出了他的一卷新作,也是他第一个长篇小说,《甑子场》既是历史的画卷,也是他自己求新求变的一个猎奇。在这个古镇上,小民走过,老财走过,义士走过,淑女走过。惟不走过的,是这方泥土,这只地球上万万万分之一的一杯风水。
读这卷小说,要买花生米下酒,同时要食洛带镇驰名的“伤心凉粉”,在惊奇动感的瞬间,一拭铅热之泪。泪水花了美人的颜,湿了壮士的须,亦然滋润了文艺的心……
《甑子场》力图刻画一个客家小镇的历史风云,将作者近些年的生活体验感觉集中表现,熔于画面,行文如行云流水,展示了作者写作高手的精湛功力与结构能力。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
——张放(著名小说家、批评家、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
《甑子场》的题材是重大的,情节是戏剧性的。诗人凸凹以诗的情怀,将其笔下的人物置于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凸显出人的命运这个大主题,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时空纵深。
“她一生中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有过感情纠葛,但这四个人都死了。”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这部小说的“点”,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与卖点。
——何小竹(著名诗人、小说家)
《甑子场》是一部向史诗致敬的小说。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命运,经由作者细腻的文字,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它既关乎爱情,也关乎人伦。变天是时代,是历史,是生存于其中的芸芸众生谁也阻挡或改变不了的既成事实。甚至,他们也无法左右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随波逐流,他们没齿不忘。而这一切,只因作者在抒写两个字:人性。因此,我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好小说。
——聂作平(著名作家、诗人、《四川文学》杂志编辑)
小说写到今天,似乎到了难以跨越的地步,困惑、迷茫一直侵扰着作家们,《甑子场》的问世,预示着另一种写作式样的可能。作为诗人的凸凹以诗性的语言对僵硬的小说叙述模式进行了一次革新,而作为作家的凸凹则以奇特的构思对传统小说文本进行了一次破坏。不能不说,小说《甑子场》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制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诗人、作家徐甲子
《甑子场》以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和多舛命运为故事脉络徐徐展开,穿越61年的时空隧道,抽丝剥茧般为读者揭开了一层层历史迷雾。如果说三个带枪的男人与一个不带枪的男人的对比几近严酷,三个带枪男人的彼此对比几近惨烈,那么四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复杂纠结更是触目惊心!
《甑子场》始终锁定龙洛客家古镇这一核心坐标,依凭社会更迭的特殊时段和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勾连穿插、辐射显形,但并非沉浸于单一、刻板、表浅的还原和复述,而是钩沉矛盾背景,矫正形态向度,放大情感元素和生活细节,深度挖掘人情的厚与薄、重与轻,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人世的荣与辱、恒与变。精巧缜密的构思,大胆奇妙的想象,张扬不羁的叙陈,诗意恣肆的交织,吊诡迷离的悬念,成就了洋洋洒洒30万言《甑子场》的异质、独特和精良。
——诗人、作家印子君
面对影响国家和地区命运的大事件,面对那些日渐隐退的风云和传奇,成都凸凹力图在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创造”历史,即“创造”“在历史的漫天尘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的小人物”的历史。所以,他既是在写六十多年前那件“大事”,更是在写“大事”中人性的善恶、欲望、真情。如此,成都凸凹以他高超的小说技艺,为我们带来一种全新的小说阅读体验。
——70后作家、《成都晚报》记者杨不易
[《甑子场》后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东北边一个叫石板滩的地方,整编集训国民党投降部队时,接到一纸调令。调令要他立即启程回成都军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报到,之后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某国大使馆武官。
朱向璃及护送他回成都军部的一个加强班,途经龙潭寺乡时,被数千叛乱分子武装拦截,遭到惨无人道的开膛剖肚、凌迟杀戮,史称“龙潭寺惨案”。惨案发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蒋介石从成都凤凰机场(亦有新津机场之说)飞去台岛不到两个月,距成都解放仅39天。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剿匪战斗正式打响;自此,平叛与剿匪这对硬词,浩大而血腥地嵌进了中国历史书写,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为腹心,龙泉、龙潭寺、西河、黄土、三岔、石盘、贾家等乡镇为依托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刘惠安是民国洛带的末代镇长,也是共和国洛带的首任镇长。《龙泉驿区志》载:刘惠安两度兼任金堂、简阳、华阳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民国政府军队路过洛带甑子场,未经他许可,不准进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边的灌县(今都江堰),后来随母去了大巴山中的万源,再后来又移居到成都平原东边的龙泉驿。以上史实,就是我移居到龙泉驿后知道的。
洛带镇隶属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潭寺亦与龙泉驿接壤。即或这样,我也是移居到龙泉驿七八年后才知道的。具体说来,我是看了《成都市志》、《龙泉驿区志》、《简阳县志》、《用鲜血建立和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简阳平息“三·三暴乱”追述》(载简阳市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简阳市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简报》)、《龙泉剿匪记》(傅全章撰写,中共龙泉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等资料,以及在写作《花蕊中的古驿》、编选《龙泉驿民间文学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图书,编剧30集电视连续剧《滚滚血脉》(改编自刘晓双同名长篇小说)过程中,才逐渐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数龙泉驿人,更大多数成都平原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国人,以及异邦的同类呢?
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文字、声像和一季一季涌至的时间落叶,覆盖了最初的非时间落叶。记忆在覆盖中探出头来,朝令夕改,又像万花筒:它是个人的记忆式态,也是集体的记忆肖像。不可靠,是记忆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只消过去三五年,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记忆。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
对此,我感到落寞、悲凉和无语。多年来,我一直深怀着这样的感觉。
仅仅是为这种感觉找到出口,仅仅是为排遣这种感觉,我竟自有了试图从时间落叶中拽出那段历史、还原那宗事件的念头和劲头。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就是不关心一切,也应当去关心碰巧出现在身边的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的漫天尘埃中消弭得无影无踪的小人物。况且,抽丝剥茧,拨雾见日,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与道德使然。
说了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吗——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为什么迟迟动不了笔?显然,对于“拽出”和“还原”,我是一个“不知道的人”。很多时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后果,更是对肤浅与轻狂的诘责与惩罚。
小说需要细节与写点,前者是小说的“小”,后者是小说的“说”。这些,我还没有找到,或者说,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们还不能说服我,更不能说服读者。
我不愿意在想象中寻找。我不愿意寻找到的东西,不接“地气”、不带“人味”。
我一直在刨食
岷山,巴山
现在到了龙泉山
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
世界上居然还存在一处
不刨食的地方
饭,张嘴就来
水,呼气即至
不见一丝丝柴禾却周身尽暖
纸是包不住火的
没关系
包不住就包不住吧
把这地方端进书中
会不会
刨刨书,满纸都是麦浪、稻香?
刨了一辈子食才知道
即或虚构一个小镇、一处气场
也有欢乐的惊慌
这首《甑子场》,是多年闲来无事游移无助日子,对我唯一的馈赠。
终于在残黄的史海中捞出了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的一段讲述文字:
“朱向璃被害史称‘龙潭寺惨案’,领头者就是当日上午围攻公安干部的乌杰。此事缘由还得从头一天说起,龙潭寺一个中年妇女到成都市区公安十三处报案,说她的女儿被当地恶霸徐银生抢走并囚禁在其家中。徐银生又伙同另一个头目巫杰找上门来,将与她女婿黄德兴同住一室的居民高云打死,黄亦被打伤,因装死才幸免于难。2月5日清晨,公安分处派出几名公安人员前往龙潭寺调查此案,并打算解救被囚禁的黄妻。不料,遭到乌杰等煽动的百余名叛匪围攻……”
老实说,我对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记忆中的“2月5日清晨”,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我一点不怀疑他记忆中那个“中年妇女”的女儿。
正是这段讲叙文字中的“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让我找到了小说的“小”和小说的“说”。
“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她”,生发了这个小说又救了这个小说的命!
“她”就是小说的第一主角扣儿。有了扣儿,也就有了“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我把“龙潭寺”和“洛带”揉在一起,虚构了一个镇名“龙洛”;我把“龙潭寺惨案”故事植入龙洛,把“三三叛乱”故事及洛带场景叠合在甑子场;将洛带镇长刘惠安作为安的原型,龙潭寺叛乱头目乌杰作为乌的原型,军统成都特务头子李才干作为菜的原型,国民党残匪马力作为马的原型……我就做了这些活儿。
对于我做的活儿,诗人作家席永君评价说:“美国人以胶卷镜像还原历史,凸凹以小说文本创造历史。这是一种绝妙的互文关照。”
席永君先生提到的美国人,是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卡尔•迈当斯(Carl Mydans,1907-2004)。卡尔•迈当斯1941年夏天沿成渝公路,从重庆到成都途经并逗留龙泉驿期间,拍了百余幅龙泉镇、洛带镇甑子场照片——本书采用的正是这些照片。感谢卡尔•迈当斯为我们拍摄了这些精美、珍稀的照片!
这是一本历史小说还是当代小说?爱情小说还是战争小说?玄疑侦探小说还是诗性寓言小说?跨文本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新写实派小说还是魔幻现实派小说?爱恨情仇还是政治幻觉?乡村叙事还是城镇物语?史诗呈现还是底层书写?……
所有的好小说都是无法归类的。但愿此论是对这本小说的量身定做。
这本小说取过很多名字:《平叛1950》《变天》《桃花与罂粟》《一变再变》《一九五○年的爱情》《桃花1950》《唇上的天气》《第一枪》《叛乱》《枪》《天气》《桃色》《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男人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完后发问,怎么可以这样写“平叛”这类重大事件和严肃题材呢,怎么可以这样叙述一个小镇的传奇故事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于小说/艺术创作/创造而言。
是啊我就这样写了。所幸,还发现了“理想的读者”。
写这个《后记》时,掐指一算,我移居龙泉驿、回归成都平原,已整整二十个年头。
这本书也许什么都不是,但对我来说,它的确是一条活过来的脐带。有了这条脐带,我与龙泉驿、与都江堰、与成都平原,才算真正粘连在一起了。
窗外阳光顺畅
山上桃花丁当
扣儿婆婆洛带晒太阳
马儿跑哇汽车唱
土著爹哇客家娘
扣儿婆婆笑笑真漂亮
2012/3/29,凸凹于成都龙泉驿